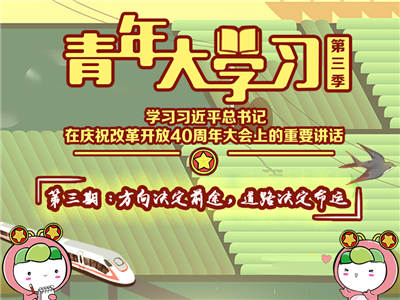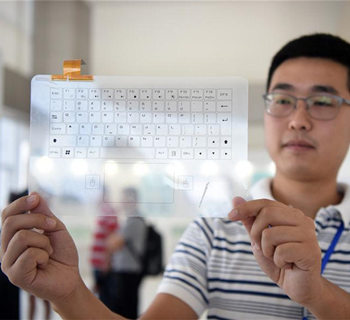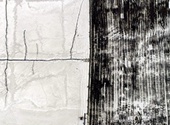-
历史的重要性,在于它紧紧连接着过去、当下和未来,更在于它既是能够被科学认知的“客观”,也是体现个体思想和情感的具体知识。今天我们谈及的“历史”二字,当然不仅指谓那些自然发生、已成过往之事,历史作为一个系统,还让我们通过绵延至今的诸种可感的对象,来发现它内在的延续性和有效性,并对眼前的一切作出必要的价值判断和预期。
良史与信史: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中国具有相当悠久的史官传统,甲骨卜辞已见“史”字,其像手执笔记事,“事”亦从“史”,且字形近似。“史”,既谓史官,也指史书。要保证所谓“君举必书”“慎言行,昭法式”,就须要求史官是“良史”、史书是“信史”。故有文字学者训“史”字从“又”持“中”,应当“书记事物”而不失“中正”,足见人们对良史与信史有所期待,更借以强调“史”的严肃性、公正性、权威性和神圣性。
春秋时期晋国太史董狐,即因能够秉笔直书而被孔子盛赞为“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兄弟为给后人留下信史,更悲壮赴死。文天祥在《正气歌》中热烈歌颂齐晋良史,正气赋予历史超越于世俗权力和价值的人文性,这使得历史在某些时候更近似于宗教信仰。
良史和信史,实际是在建构和维护一种秩序,或曰“终极依据”。任何文化在面对基本观念和主体意识的问题时,总会依据某些原初性的系统加以诠释和演绎。知识和思想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趋于丰富和复杂,“传统”变得岌岌可危,“当下”产生了许多不可抗拒和预料的裂变,这时,历史及其叙述者需要重申那些“道”“德”“理”“法”所代表的稳定性,由此发挥它的影响力。
鉴往知来:他者监督与自我约束
学者饶宗颐指出,近东古史多呈现为胜利者的自我表扬,如波斯之最高王者动辄自称“万王之王”,像这样的历史记录,仅是为胜利者服务,而中国则不然,比如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天地贤圣怪物行事,以存鉴戒,其渊源则是伊尹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这正是中国史家的优良传统,不容忽视。
历史传统之“往”的可知,又为后来史官据实记录评述君主言行提供了心理支持和行动依据,从传说中伊尹分人主为九等,到楚先王公卿祠庙图绘以存鉴戒,再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谓的“诬上”,都可视为对君主构成的一种监督和舆论压力。据《资治通鉴》载,唐太宗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可否观览自己的《起居注》,遭到后者拒绝,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亦记之邪?”褚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
唐太宗不愧一代英主,他认同褚遂良所言,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要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看到古代王朝兴衰,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此约束自己不善的言行和政令,才有令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可见,就当事者而言,历史绝非仅是有关过去的知识,它实在能够助力预见和创造真实的未来。
“青山青史各千年”:记忆的永恒
历史从不超越于人们的现实而存在,生活本身就是历史,我们思考的问题、思考问题的方式及其结果,都笼罩在“历史”之中。研究历史、写作历史因此变得有意义,历史天然应当获得我们的重视。古往今来的历史学者们,大多有着极强的洞察力,他们看到历史中贯穿始终的那种永恒性,因而自信能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实际也依赖于有着共同生活经验和记忆的集体的“公心”。
元人王鄂在一份奏折中申说编修辽史和金史的重要性:“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兼前代史书,必代兴者与修。盖是非与夺,待后世而可公估也。”国(王朝)在史的面前,显然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时段,历史的存在是永恒的,而有关这个永恒的叙述,需要一种“公估”。历史不可随着王朝以及民族国家的覆灭而消亡,也成为历史学者的共识。陈寅恪曾总结,前代学者的学问人品虽不能一概而论,但他们心中存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共同观念,却是不言自明的,他又说道:“国亡然能有史,则殷鉴不远。从善去恶,国可再建。如无史,何所鉴戒?何所取法?华夏民族无从因袭,将不复存在矣。”历经神州陆沉的变局,陈寅恪考虑最多的早已不是个人的安危荣辱,而是国家兴废和国史存亡的重要议题。
“一春旧梦散如烟,三月桃花扑酒船。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这是《台湾通史》的作者连横在泛游杭州西湖时写下的一首绝句,生活、自然、历史,在此浑融为一,历史最易引起人们兴感,它与山川日月一样永恒不灭,它又在不断警醒和提示我们的同时,制造出许许多多的“意料之外”,正像是飘散如烟的“一春旧梦”,既真实不虚,又迷幻如影。
【编辑:贾志强】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中央政治局同志向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述职
- 习近平:在新的起点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习近平为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
-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 人民日报评论员: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基本遵循
- 山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 党的十八大以来污染防治纪实
- 绘蓝图勇担当 习近平16字要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 微视频:点亮
- 习近平这样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内蒙古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两会重要讲话精神纪实
- 总书记这篇文章,让我们读懂全面依法治国
- 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新年首会 干货全在这里
- 【领航新时代】湖南:从难点入手 向短板发力
-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习近平主持召开的这个会议划出重点
- 习近平时间|让网信事业更好造福人民
- 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 【领航新时代】黑龙江:在春天启航 用四季歌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