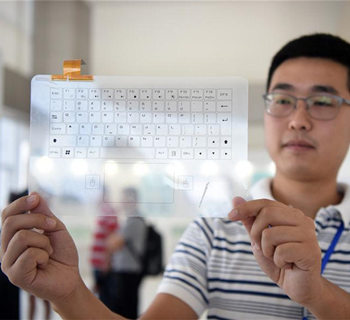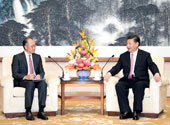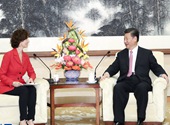-
当3倍的孤独从天而降时,这个三胞胎之家一点点被压垮了。
最先崩裂的是时间。自三胞胎儿子被诊断为孤独症起,父亲刘洪起和母亲就失去了自己的时间——漫长的寻医问药和24小时不间断照料接管了他们的生活。
家庭关系也紧跟着龟裂,循环往复的争吵、哭喊、埋怨之后,母亲选择离婚,离开了这个“最孤独的家庭”。
接着破碎的,是这个家摇摇欲坠的空间。父亲带着儿子搬了3次家,从打工的天津塘沽区搬到热闹的河西区,再搬回津南区的农村老家,最后搬去镇上。他跟邻居打过架,也低头道过歉,还曾紧锁门窗,把全家人严实地关了起来。
刘洪起用了10余年来消化命运开的这场玩笑。
17年过去,三胞胎长成了个头近1米8的大小伙子,这个53岁农村父亲的诉求却一降再降,一开始他奔着治愈而去,找最好的康复训练;再后来,耗尽积蓄的他盼着孩子能吃饱穿暖健康长大;如今被疾病和衰老挨个儿找上门的他,愿望只剩下一个,“要让孩子活下去”。
一
厨具零散地放置在地上的各个角落,厨房水池里结出了黄褐的油垢。几百个瓶盖垒在卧室一角,那是老三最爱的玩具。卧室的另一头是3块床板,枕头、被子和墙壁上都泛着黑色的污渍。
飘荡在这间几十平方米小屋的,是“嗯”“啊”“哇”的交替高喊,和锅碗瓢盆被踹得噼里啪啦的声响。刘洪起习惯坐在凳子上,盯着三个孩子,不时起身给三胞胎擦屁股、擤鼻涕或是拉开正在打架的3人。
这个中年男人坦承,自己“恨过孩子他妈”,而且是“发了狠地怨恨”。
孩子3岁时,夫妻俩发现了不对劲,三胞胎不会讲话,顶多蹦出一个字,走路也是歪歪扭扭的。他们抱着孩子四处求医,什么偏方都信,吃了“不知道有多少”的药,却始终不见病情转好。
后来,有医生告诉夫妻俩,三胞胎可能患了孤独症。这个家庭行进的方向硬生生转了个弯。妻子被迫辞职回家照看孩子,塘沽区小有名气的修理工“小刘师傅”不再约人喝酒吹牛,也不再去洋货市场溜达“淘宝”,只加班加点地干活。
确诊那天,他最后一次主动买了啤酒,3元钱的啤酒他一饮而尽,“从今天起再不能乱花一分钱了。”
家也变了。有一次下班回家,留给他的是被开水烫伤的儿子,和神情呆滞的妻子。
孩子长到五六岁时,依旧没什么起色。“受不了了”的妻子决定把孩子送回河北的农村老家,那里有“专门的地方照顾孩子”,一旦送走,夫妻俩还能像过去那样,在天津安心打工挣钱。
刘洪起没能拗过态度坚定的妻子。一次,他叫上妹妹刘洪萍一道去河北探望孩子,发现孩子在吃塑料皮都没有剥开的火腿肠。宿舍里,枕头上有一滩血迹,孩子天天流鼻血。刘洪萍说:“哪能把孩子送到这种地方自生自灭啊。”
夫妻俩离婚了。
刘洪起接走了三胞胎。后来,他辗转得知,天津“童之舟”儿童教育中心有专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课程。这个父亲没问学费,就辞掉工作带着三胞胎把家搬到了市里的河西区。
他已经来得太迟了,医学界普遍认为,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黄金时期是2至6岁。可身边没有人懂得这些“常识”,这场和时间赛跑的比赛,他输在了起跑线。
机构创始人黄冬莹旁观过成百上千个因为孤独症被拖垮的家庭。自1943年美国男孩唐纳德被确诊为孤独症以来,医学界在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没能厘清其发病原因,也找不到任何一种有效治疗的药物。这个病可以轻易拖垮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孤独症家庭。
据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的报告,孤独症的患病率为0.62%。黄冬莹的儿子就是这0.62%。
那时她已开办康复训练机构好几年,却从未见过一个家庭塞下了3个孤独症患者,她为这个家庭减免30%的学费。
父子4人最终坚持了10个月。只出不进的积蓄被彻底耗尽,刘洪起带着孩子沉默地离开。原本,接受专业康复训练的三胞胎已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好转的迹象,可他没有钱再继续了。有人建议这个中学学历的父亲,回到户口所在地申请低保,起码别把孩子饿死。
回到农村老家后,刘洪起发现,自己好像没那么恨妻子了。
孩子的力气越来越大,很多时候连他也治不住。只要稍稍离开,三个孩子都可能扭打在一起。同样的话他每天说上百遍,孩子没有反应。十几岁的孩子吃饭还会被脆骨噎住,差点呛死。
有一次,他发现存折不翼而飞,看着不远处的老二,刘洪起以为是儿子弄丢了存折。他抱住老二,用手狠狠抽打儿子的屁股。老大老三瞧见了也冲过来,父子四人打成一团。打着打着,老二哭了,老三哭了,刘洪起停手,抱着儿子嚎啕大哭。
“她能坚持活下去就不错了。”刘洪起自嘲地笑了笑,说自己终于理解了妻子,理解了那种眼睁睁看着一个家庭破裂却无能为力的感觉。
二
回到童年成长的村落,刘洪起感到一种异样的隔阂。他带着孩子出门散步时,总有邻居“指指点点”,“嗬,3个傻子”“你天天带3个傻子跑嘛呢?”
他从不回应。这个父亲很清楚,孩子是“异类”,只有低调才能安稳度日。回老家前他们习惯踩踏着走路,不分白天黑夜,这样总会发出很大的声响。有时候半夜睡醒了,三胞胎会兴奋地一起嚎叫、玩闹。每次碰到邻居稍稍露出欲言又止的表情,刘洪起都一个劲儿地说对不住。
他管不住孩子,唯一能做的,就是把门窗关紧。后来,他得了失眠的毛病,有时候熬到天亮才入眠。
但邻居似乎并没有要接纳父子4人。刘洪起发现,自家空地不知何时垒了一大堆邻居的杂物和垃圾,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他让人挪走,对方不肯,双方扭打在了一起。
刘洪起躺在地上,3个孩子像是被吓着了,缩在墙根。老三咿呀哇呀地喊着、比划着。村民于有芝匆匆赶来,看到3个驼着背蹲缩的孩子木讷、萎缩又害怕的神情,难过得想哭。这个中年女人和丈夫常为三胞胎做些烙饼、饺子和包子。
“我都不敢想这些孩子平时经历了什么。”她说。
她再去探望孩子时,三胞胎越来越沉默。院子里遮天蔽日的大树挡住了阳光,也成了毛毛虫和蚊子的天堂。给孩子换衣服时,她发现孩子背上爬了好几条毛毛虫,红疙瘩密密麻麻,孩子却一声不吭。她惊讶地叫出了声,随后又哭了出来。
家里的门窗被封得死死的,孩子们活动的空间从整个村子缩减到了自家院落,又缩小到了一间几平方米的卧室。夏日晴天也紧闭大门、拉紧窗帘,开着白炽灯照明。三胞胎坐在瓶盖组成的玩具堆里,沉默地玩着。
屋子里潮湿又闷热,她和孩子的姑姑刘洪萍把屋子彻底清洗了一遍。父子4人盖一床被子,挤在不到2米宽的床上,连翻个身都很困难,被罩里还有排泄物的痕迹。厕所的味道让她差点晕过去,两个人忙了一天。回家后,她躺了两天才有力气下床。
她突然理解了刘洪起的话。“我们爷儿几个啊,那就是相依为命。”“嘿,我们能活下去就不错了。”
这个微信取名为“儿子的港湾”的男人,已经没有了任何私人时间,他总是忙着做饭,要看着孩子们吃完才安心。他十几年没去体检过了,因为害怕查出什么病。
他的情绪一点点被抽干、麻木,唯一还保留的个人爱好,也许是喝可乐。自从孩子得病后,他戒了酒,反而爱上了年轻人喜欢的可乐, 那东西,“甜啊”。
一次,他告诉妹妹,自己早就想一了百了,可想一想,又下不了这个决心,“我不在,这3个孩子咋办,能留给谁啊?”
孩子的姑姑把眼泪咽回去了,她跑到门口,把窗户和大门大打开,冲着哥哥喊,“不准关门了,要通风!通风!”
三
刘洪萍知道,哥哥心里紧闭的窗户没有真正打开。白头发和皱纹迅速地找上了哥哥。他“只有53岁,看着却像个60多岁的人”。
给人做家政服务的刘洪萍后来想,也许能支撑哥哥的,不仅是3个孩子,还有他的性格。
曾有人想给三胞胎做募捐,刘洪起拒绝了,“募集一次还行,两次、三次呢?这是个无底洞,我不能拖垮更多人了。”他笑着跟人说:“还没到那个程度,有低保呢,别担心。”
于有芝给他家运食物的小红桶被三胞胎当成了马桶,在里面拉屎撒尿。刘洪起发现了,二话不说买了两个新的送回去;亲戚朋友结婚给他打招呼不必随礼,婚礼当天,他还是拿着红包出现了。
前两年,因为村里的老屋被认定为危房,又考虑到这个特殊家庭的情况,当地政府在北闸口镇为一家人租了一间小房子。
虽然见到孩子的次数少了,但于有芝发现,三胞胎变开朗了,脸上的肉也多了。三胞胎还会驼背,有时也记不住擦屁股,可见到她时,活泼的老二会拍拍于有芝的肩,示意“打招呼”。
这家人同一楼层的邻居中有位因“糖尿病足”而截肢的老人,老人独自生活,极少出门,买菜都花钱雇人。刘洪起看不过去,有时搀扶老人下楼,有时顺手帮忙买菜。老人给钱,他拒绝了。
在老人身上,刘洪起有“同病相怜”的感觉。20多年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工厂做零配件生产。他的同事中有不少人是残疾人。很多人和他称兄道弟。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一群正常人,就是需要多一些帮助而已。”刘洪起说。
邻居问他,“老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啊?”还有人背后嚼舌根,说刘洪起不过是“图老人的家产”,这些话他都不在意。听完笑笑,他招呼上3个孩子,自己扶住老人,5个人浩浩荡荡地下楼。
平静生活里的唯一插曲是时不时蹿起的血压。有些时候看到孩子做错了事,他着急地大喊,突然感觉头晕目眩,站也站不稳。一次,他彻底晕了过去,刘洪萍打来电话,老大接了,电话那头却是“呜呜哇哇”的声音,听着急切。
刘洪萍决定把哥哥“撵”出屋子,她带着哥哥一起去听“模仿邓丽君”的演唱会。有时让哥哥开电动车载上三胞胎,一边儿兜风一边儿玩,自己在家里收拾屋子做饭。“必须给他减压。弦一直绷着会断的。”她说。
于有芝是个快嘴,常给这家人送吃的, “我们去就是告诉那些人,还有人愿意来串门,别想欺负他们。”
三胞胎一天天长大了。刘洪起想过以后在村里教三胞胎种花,也想过找一个没那么多歧视的地方,教会孩子打扫卫生,干活挣钱。
他一天天老了,这个问题依旧没有答案。三个孩子在特殊教育学校的毕业一拖再拖,他不敢让孩子毕业,因为“毕业了就没地方可去了”。
这名白发丛生的父亲坚信,只要还没毕业,孩子也许就能逐渐掌握生活技能。哪怕速度很慢,但对于照料孩子吃喝拉撒已筋疲力尽的他来说,这是必须紧紧攥住的希望。
只是,他不确定,衰老、病痛、死亡和3个孩子的成长,哪一个会更早到来。
四
和很多孤独症患者的父母一样,刘洪起一直在追赶时间。他已经追了14年,还是不能停下。
一群拥有相似经历的父母,时常会讨论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命运。最新的一个故事是,一个15岁的天津孤独症孩子失踪了整整两周,最后在北京顺义被找到。没人清楚他如何跨越了100多公里,这个孩子每天去快餐店捡剩下的食物,被人发现时,他又瘦又脏,看见警察扭头就跑。
离家出走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反感母亲对他的管理方式——这个要上班的单亲妈妈选择把孩子关在家里。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孤独症患者的需求会变多,想法也会变得丰富,但社会和父母并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黄冬莹说,很多父母选择简单粗暴地和孤独症患者相处,久而久之,那些患病的孩子情绪无法抒发,有人砸东西,有人逃跑,有人打家长,也有人自残。
类似的故事在这个充斥着眼泪的圈子里一点儿也不罕见。 一个成年的孤独症患者,因为情绪激动经常伤人,家人无奈用铁栏杆锁住房间。家人在房间里只放了一张床垫,铁门里开了一个窟窿,每日定时送饭。一到夜里,孩子精神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捶墙捶门。
黄冬莹说,媒体报道了这家人好几次,依旧没有解决的办法。这家人很穷,精神病院送不起,只能一天天这样拖着。
每次听到这样的故事都会让刘洪起叹气,可他能做的实在不多了,为了追赶孩子成长的时间,这个父亲终于也变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模样。
这个曾经讲究公事公办的人,为了多留孩子的课桌一年,他跑去特殊教育的学校求老师和领导,甚至像膏药一样紧紧贴在领导后面。
这已经是三胞胎第二次延期毕业了。支撑他一次又一次往返学校的理由,是他眼里那些笨拙的成长——三胞胎的亲姐姐带着公婆来家拜访,提了几串香蕉。落座后,老二到桌子前,掰开香蕉,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自己饿了想吃东西,可他把掰下来的香蕉递给了两位老人。
刘洪起发现,自己说了几千遍的尊老爱幼,也许这个孩子真的听进去了。老师告诉这个父亲,学校里,老二也“很有服务意识”,课间会带着所有比自己个头矮的孩子去厕所,一个接一个地排队。
一家人吃饭,个头最壮实的老二会主动给哥哥和弟弟夹菜,老大被陌生人叫到名字也有了反应,有时,他会笑,还会扑进爸爸的怀里。
于有芝带孩子买冰淇淋,他递给老二一根,对方不接,给两根,还是不接。她突然明白了,抽出三根,老二收下了冰棍,一溜儿就跑没影了。
在黄冬莹看来,想要解决刘洪起一家乃至大龄孤独症患者安置的问题,靠公益组织和个人并不现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她曾和一批“同类人”共建了一个“大龄中心”,专门托养这群大龄孤独症患者。因为缺少足够数量的专业老师引导,大龄孤独症患者情绪无法抒发,有人砸玻璃,有人打架,有人胳膊被划破,也有人去了第一天鼻梁就被撞破了。
“大龄中心”最终草草收场,她把孩子领回了家,让儿子天天练字打发时间。没过几天,这家“大龄中心”竟然又“活”过来了,还是那批父母办的。她问对方,为啥啊。
“没办法啊。能搁家里吗?”一个家长说。
帮助了数千名孤独症儿童接受康复训练的她,在给儿子寻找出路这件事上和刘洪起没有太大分别。在国外普遍适用的庇护性就业、支持性就业和支撑安置三条出路,在国内还不多见。
从事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16年的黄冬莹坦承,国家近年来对低龄孤独症患者康复训练的重视程度已经大大增加,但对变大变老的孤独症患者的去向,依旧缺乏关注。
黄冬莹还是想问: “那些大龄孤独症患者消失了么?”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天津北闸口镇镇政府相关工作人员。对方表示,目前镇政府对刘洪起一家在房屋、最低生活保障、心灵帮扶等方面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帮助,他们也正试图为这家人提供更多物质上的援助。
刘洪起说,不管怎样,现在都还远远没到放弃的时刻。就在前些日子,刘洪起打开大门,准备把住在隔壁的残疾老人接上,一起下楼转转。他朝里屋喊着,让儿子快一点出门。一扭头,他傻眼了——老二,那个“咿呀哇呀”不停、脾气最大最容易发火的少年,正搀扶着老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缓慢地下行。
儿子和老人都扭过头看他,两个人笑着,他哭了。
【编辑:贾志强】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提前看!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出访
- 微视频《金砖之印》
- 习近平这样向世界讲述中国
- 5年来,习近平这样说“金砖”
- 靠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 识才聚才用才 习近平开创人才工作新风
- 习近平要求用这“三激”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深入
- 国企怎么改?习近平的这些话很明确了
- 落实新时代好干部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说
- 中非合作发展新时代
- 习近平点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
- 旗帜鲜明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 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
- 习近平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致贺信
- 英才聚神州!习近平厚植新时代人才沃土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阿读者会在阿联酋举行
- 这里是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弯
-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在这三个方面作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