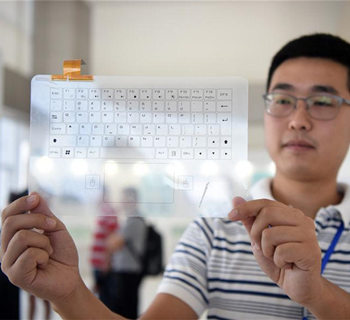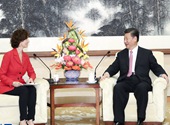-

因为摄影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任曙林的名字为很多人所知。没人能抗拒他照片里的容颜和身姿,时过境迁,仍然美得让人嫉妒。凭什么上世纪80年代的中学生就那么好看?
日前,任曙林在接受专访时说:“人们喜欢看那会儿我拍的高考照片,不是想看高考,而是想看人,想看一个人在年轻时那种鲜活的、自然的、属于他本身的状态。”
任曙林对拍摄中学生群体的自我要求是,“一定要拍得像这个中学生,实际上就是像人本身”。
“真实的东西是有力量的,你看那会儿的孩子多轻松,当然那会儿高考对他意味着什么可能跟现在有差别,但是根上的东西还存在,还是十七八岁的青少年。”
因为1979年一次“阴差阳错”的经历,任曙林开始将目光投向高考现场。那是夏天的早晨,单位同事突然告诉他:“今天高考,你不是喜欢照相吗,还不去。”任曙林当时的反应是“激灵一下子,抄起相机”就溜出了单位。有一所中学考点在家附近,任曙林赶到那里时,考生正在进入校门。
透过教室后门的瞭望孔,任曙林看到这样的情形:“桌椅单行摆放,老师用脸盆打来水,把它撩在间隔的地上,降降温吧……教室前面的讲台上,有几个白瓷杯子,没把儿,杯口上方有一圈蓝道的那种,谁渴了,举手,老师会送水过去。”到了1980年高考,任曙林还搞到了监考证,幸运地进到考场里拍。
关于那几年的高考,有一个场景令任曙林记忆深刻。某个中午,在两场考试的间隙,他看到几个女生就在胡同阴凉处休息,看着自行车,站在那儿,“现在考生早去五星级宾馆睡去了,不会是那样的”。还有不少考生喜欢去阴凉通风的自行车棚复习,“北京7月的中午,蝉声此起彼伏,柳条儿摆动却没有风声,早晨观阵的人们不见了踪影,默念背诵的窃窃声,断续地传到我的耳朵里”。
任曙林感叹,那样的画面会让你感觉到,他是一个无比鲜活的人,他的喜怒哀乐特别接地气。

任曙林摄影作品《八十年代中学生》。新星出版社供图
“我觉得这里头不光是一个考试,对青少年这个年龄段我特别有兴趣。考试只是中学生的节点,高考对他来说是一个结束也是一个开始,但实际上这里还有很多东西。”从1979年至1981年,任曙林连续拍过3年高考。短短几天的高考拍摄很快结束了,任曙林对中学生的拍摄却延续了下去。
“学校有数不清的瞬间,虽然很快,但特别吸引你。”任曙林说,当年之所以将镜头对准中学生,是因为这个群体,校园的这片试验场地,藏了很多他在摄影上想找的,甚至摄影之外想找的东西,“有些想法、想说的话,通过中学生这个群体能够说出来,把自己的一些梦或理想寄托在那里”。
最近在任曙林的新书《不锈时光》分享会上,编剧、影评人史航提到,他感觉摄影师进校园拍照是很刺激的事,毕竟镜头对于学生而言,是一种潜入者,所有的学生都会像雷达一样警惕。史航很好奇摄影师如何变成“透明人”,让学生放下遮掩的本能自然暴露在镜头面前?
任曙林认为,进入一个不属于你的群体或者时空,需要对得上“暗号”,摄影师的职业、专业、执着和善意等诸多元素综合起来,解除对方的戒备,从而取得认可。“体态、语言、神态和这个群体保持一致,让他们感觉到你不会产生威胁、觉得舒服、产生放松感,摄影师自然就变成透明的了,这是一种基本功。”
任曙林当年进校园拍照,给自己规定了一条基本原则:不跟学生交流。“语言会干扰摄影。摄影是视觉的东西,要尽量让它纯粹一些,可能走得远”。
“大家比较熟知那张男生女生隔了两排桌子坐着的照片。当时我就知道放学之后教室里肯定会有这样的画面。我进教室是轻轻地推门进去,一扫就看见了。他们意识到我进去了,知道我肯定不会照完相之后送给老师或家长,而且也知道这个人特别专业,就把他们征服了,这样你就会很自然地拍到。”
对于任曙林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不可替代之处是一种整体的氛围,天时地利人和。“这不是人为造成的,就是历史条件到一个节点上,聚足了时间、空间。”
有很多人后来对任曙林说,任老师,没有你的记录我的青春就没了。“现在他们会说,我那会儿还有那个动作?还有那个表情?多好!他自己全忘了。”
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的摄影条件,如今人手一台手机、数码相机,摄影随时随地轻松发生。但任曙林很在乎的是,人们能否认真地感受生活,真正拥有发现美的眼睛。
“眼就是心灵的窗户,眼睛靠心灵支撑,如果你没有心灵,这个晶状体是没有用的,是睁眼瞎,摄影就解决这个问题。”
任曙林觉得,摄影,本质是一个完全不依赖你而存在的时空,你又在里头看到了自己。“摄影是一种感知方式,感是感觉,知是知觉,它开辟了一种认识自己和认识周围世界的通道。”
【编辑:贾志强】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习近平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盟委员会主席
-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 习近平会见世界银行行长
- 习近平向尼雷尔领导力学院奠基仪式致贺信
- 英才聚神州!习近平厚植新时代人才沃土
-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阿读者会在阿联酋举行
- 这里是九曲黄河最后一个弯
- 习近平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在这三个方面作表率
- 习近平总书记贺信在求是杂志社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 习近平要求乡村实现“五个振兴”
- 饮水当思源 先富帮后富
- 习近平向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致慰问电
- 习近平讲话引台各界热议:“感性呼唤 理性招手”
- 习近平时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中国青年运动潮平岸阔 风正帆悬
- 习近平就巴基斯坦发生严重恐袭事件向侯赛因总统致慰问电
- 习近平: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 总书记告诉你,什么样的才是高素质干部
- 习近平:如何成为一名合格党员
- 【央视快评】人心所向 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