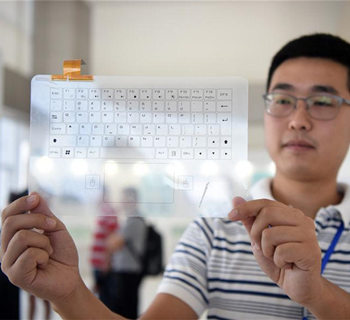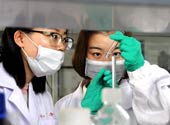-
她们的遭遇所对应的那段民族共有的伤害和屈辱史,不应该通过沉默与遗忘来“化解”。
又一位“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离世。据媒体报道,1月23日,李爱连老人在山西武乡县家中去世,终年90岁。
李爱连老人生于1928年,山西省武乡县人。抗战期间,她曾两次被抓到据点,被迫成为日军性奴隶。1946年,日军还一直占领着当地的南沟,李爱连被关押在南沟据点几十天,直到日军撤离据点,她才得以回家。
这段经历给老人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很长时间内她都不愿与人聊起这些往事。在2017年上映的电影《二十二》中,她对着镜头回忆了被日军凌辱的过程,拍摄过程中,导演曾因为老人的叙述太让人痛心,表示拍不下去。她离去以后,影片所记录的22位老人,幸存于世的只剩下7位。
作为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的受害者和见证者,“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就是活着的历史。她们每个人的离去,都令那段历史叙述少了一分生动性。受制于生命规律,“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最终都将离开这个世界。可作为一种历史的刻度,她们的离去,并没有带走“历史”,也绝不应该导致生者遗忘历史。
“慰安妇”制度受害者不是一个抽象的标签和符号,而是活生生的人与历史。在电影《二十二》里,不少“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已经不太愿意提及和触碰那段历史。对于具体的受害者个体而言,沉默或可视作是一种岁月沉淀后的“自我疗伤”,但她们的遭遇所对应的那段民族共有的伤害和屈辱史,不应该通过沉默与遗忘来“化解”。
现实中,“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不仅面临着生活上的困难,也承受了太多不应该承受的道德压力。比如,戴“有色眼镜”看待“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群体的观念仍多多少少存在;电影《二十二》播出后,片中的人物截图竟被制作成了轻佻的表情包;再比如,2016年,上海“海乃家”慰安所面临拆迁,引发争议,有人认为该留,有历史意义;有人认为该拆,“慰安所”在上海很多,这个不一定要留下,且该建筑位于学校旁边,影响不好;有的学生觉得难以启齿……
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民间力量开始正视那段历史,关注“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的生活境况,但这显然还不够。历史学家托克维尔说过,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铭记每一位历史悲剧事件受害者的遭遇,在他们幸存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人道关怀,并通过他们的个体遭遇,通向对更广阔历史真相的理解和反思,这是“让过去照亮未来”的基本路径。铭记“慰安妇”制度的历史,不是为了强化仇恨,而是要避免悲剧的重演。
对于仍在世的几位“慰安妇”制度幸存受害者而言,我们对那段历史的铭记与记录,能够赶上他们“凋零”的步伐吗?终有一天,他们都将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不是意味着关于那段历史的记忆,也将彻底烟消云散?在遗忘到来前,我们还有哪些该做而未做的,我们能否做得更多?
【责任编辑:齐琪】 -
相关文章
- [ 01-24 ]
- [ 01-14 ]
- [ 01-13 ]
- 热点新闻更多>>
-
- [ 01-24 ]
- [ 01-23 ]
- [ 01-24 ]
- [ 01-24 ]
- [ 01-23 ]
- [ 01-23 ]
- [ 01-23 ]
- [ 01-23 ]
- [ 01-23 ]
- [ 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