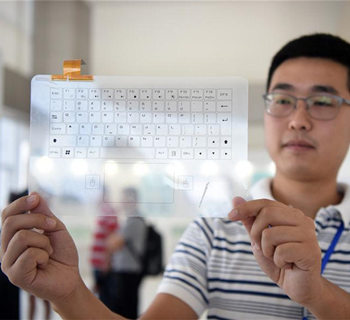-
赵海鹏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中国大鲵,是在2014年贵州省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附近。他们已经很久没在野外见过野生大鲵了,这一发现让他所在的科考队格外兴奋。
这种俗称“娃娃鱼”的生物,学名为“中国大鲵”。经过数亿年保持至今,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生物界的“活化石”之一。
多年以来,生物学家一直将大鲵划分为中国大鲵、日本大鲵、美洲大鲵3个物种,其中中国大鲵处境最为危险,早在2004年就载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属于极度濒危物种。
但是,这只4年前发现于梵净山脚下溪水中的“野生”大鲵让人们大吃一惊。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领衔的一支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基因比对发现,这只大鲵并非贵州当地“土著”,而是来自陕西。
两周前,他们公布了一项历时10年的研究结果:一直被视为单一物种的中国大鲵至少由5个隐存物种组成。
这一发现意味着本已危机四伏的中国大鲵保护工作面临更大的挑战——近年来,规模化养殖、野外放归等一系列“保护”行为,也许直接污染了大鲵不同物种的基因独特性。
1.7亿年前的侏罗纪时期,大鲵与恐龙为伍时,人类的祖先尚未诞生。这种行动迟缓、性情温顺的两栖动物躲过了小行星撞击地球,经历数度物种灭绝和新生,存活下来。
这一次,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当代生物学》上的论文标题就是,《中国大鲵揭示隐存物种的悄然灭绝》。
“这一结果让我们一下子坐到凳子上,目瞪口呆”
经过近10年的考察,中科院昆明动物所与国内外多个科研单位和林业部门合作,在全国范围内收集到70个野生和1034个养殖的中国大鲵样本。
其中在2013~2016年,多个科研单位曾参与一项调查计划。4年间,各地区科考队在16个省97个县可能的大鲵栖息地开展独立调查。
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他们只在4个县找到了野生大鲵,共计24只;而在这些河流周边1000米范围内的问卷调查表明,当地居民上一次见到大鲵的平均时间是19年前。曾经广泛分布在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大鲵,不知从何时开始没了踪影。
“找到一只野生的日本大鲵平均需要1.2小时,美洲大鲵需要2.2小时。找到一只野生的中国大鲵平均要花上4个月。”他们在一篇研究论文里说。
在中国民间,因为叫声像婴儿啼哭,大鲵被赋予“娃娃鱼”的昵称。“娃娃鱼”一度被视为不祥之兆,逃过了人们的口腹之欲。
在调查期间,赵海鹏的老师回忆起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河南某山区所见大鲵繁盛的情景:“村里举办婚宴,每张大圆桌都能端上一盘大鲵,还是婚宴前夕临时捕捉的野生个体。”这段回忆也暗示,中国大鲵的命运从那时起已面临威胁。
2007年起,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对中国大鲵物种开展了野外调查及遗传谱系学研究。该所研究员车静告诉记者,考虑到两栖类生活特性,迁移能力差,另外,中国大鲵各自生活在独立的水系中,理论上讲应该有很大的遗传分化,甚至包含隐存独立种。
仅凭肉眼观测,很难从大鲵极其相似的体貌特征辨别出它们的差异。此外,多年来人为迁移造成大鲵种群的混淆和杂交现象,仅凭形态观测,更是难上加难。进行基因鉴定是可行的方法,但也面临困难。大鲵基因组是由大约500亿个碱基构成,人类基因组的碱基数为30亿个左右。目前限于技术,很难组装出中国大鲵的全基因组序列。
后来,基因组测序技术的发展,为认识这种生物带来了新的契机。
据车静介绍,在此之前,中科院昆明动物通过线粒体基因片断分析,发现中国大鲵有7个支系。但是线粒体不能代表基因组水平,难以一锤定音。
做简化基因组数据分析时,车静发现,有5个支系从准基因组的数据上看已经产生很大的分化了。如果它们在野外异域分布,没有人为因素把它们放到一起,它们永远不会相遇。
他们发现不同支系的中国大鲵已经在野外分别演化了471万年~1025万年,经过这样漫长的时间,不同的种群很可能已分化为独立的物种了。也就是说,中国大鲵至少存在5种完全不一样的隐存支系,“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物种分化的水平”。
简化基因组数据分析结果,让全组成员都十分震惊,车静形容:“这一结果让我们一下子坐到凳子上,目瞪口呆。”
新发现的5个隐存物种按目前的大概分布,分别是陕西种、四川种、广西种、贵州种和安徽种,分布地与水系分布紧密相关,大致对应黄河、长江、珠江及钱塘江等水系流域。
车静非常清楚,这证明了一个长期的猜测:这些分布在五湖四海的娃娃鱼虽拥有同一个称谓,漫长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阻断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如今它们已经完全不属于同一个物种。
新发现牵动了世界同行的神经,但车静没有多少自豪之感,因为更严峻的问题接踵而至:此前从未证实如此巨大的遗传分化,中国不同地区的大鲵长期被视为一种。无论人工养殖,还是政府鼓励的增殖放流保护,都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但现在看来,这些保护隐藏巨大的风险。“保护”直接导致的后果,很可能是基因同质化,也许其中一些隐存物种已经遭遇灭顶之灾。
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原则,是“最大程度保护遗传进化的独特单元”。
“野外什么也看不到,全部都在养殖场”
在见到那条野生大鲵之前,全组人员已经在梵净山的苦竹坝搜寻了两天。这里是列入规划的大鲵保护区。全国针对中国大鲵的保护区共有33个。
伦敦动物学会爬行动物组负责人本·塔普利也参与了调查,最让他吃惊的就是,即使在这样的区域,见到的野生大鲵居然这么少。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之前也做过一些极危两栖动物相关工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相对比较容易找到目标物种。相反,中国大鲵作为这么大体型的生物,居然这么难找,实在令人惊讶。”
科考队里上了年纪的专家还记得,小时候在山涧里,常常可以见到大鲵。“但现在的孩子看不到这一景象了。”车静伤感地说。
寻找野外大鲵时,科考人员需要穿上潜水服或下水衣,夜间踏查需打着手电筒,在没膝乃至及腰深的溪水中溯流而上,不放过任何一个洞穴、石缝和草丛。
同行的伦敦动物学会专家给团队成员留下深刻印象。每到一个点考察,他们会建议大家将车远远地停在路边,下水之前,从头到脚包括工具一律消毒。调查中遵循的原则是,即使做科研工作,也要努力防止给任何地方带去污染和传染病。
在梵净山,是装着沙丁鱼和鸡肝的诱捕笼带来了好消息。第一天查看时,笼子空空如也。第二天,前去查看的队员惊呼起来,一只野生大鲵落入诱捕笼里。
这是一只长约四五十厘米的大鲵,身上有着典型的疣突,安静地趴在笼子里。研究人员将它标记、称重、测量,取得基因和病原体样本之后,按照规定交给辖区渔政管理部门。
这只大鲵并不算最强壮的类型,但足以让所有在场者感到兴奋。两年后回忆起那一刻,本·塔普利依然记忆清晰:“那天早上,我们又冷又累,情绪不高。但这样的时刻让你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在野外见到这惊人的生物,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保护这一神奇物种的决心。”
当时他们没有想到,这只大鲵不是贵州“原住民”。它的故乡是陕西。参加考察的团队成员推测,它很可能来自附近的养殖场,趁着雨季涨潮时逃出牢笼,或是在某次放流中存活下来。
野生大鲵难觅踪影,养殖场里则是另一番景象。“有个怪象就是野外什么也看不到,全部都在养殖场,成千上万。”车静说。
许多人见过养殖场里被圈养的大鲵。那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颜芳向记者描述,身材巨大、四肢娇小的娃娃鱼拖曳着尾巴,被困在一个个用水泥砌筑的洞穴中,它们的卵放在篮子里抚育,“像一枚枚光洁的银币”。据介绍,大鲵在人工养殖的条件下无法自然产卵,到了交配季节,只能靠催产素催产交配。
作为珍贵物种,中国大鲵曾在20世纪60年代为国家换取过大量外汇,但那时政府定点收购的都是成熟个体,野生大鲵的种群没受到致命的冲击。大鲵的养殖合法化始于20世纪70年代。市场需求强烈刺激了人工养殖,农民捉到野生大鲵,会卖给人工养殖场,最贵时一公斤可卖1万元。
科考队从养殖场采样,并不比野外采集容易多少。虽然许多大鲵养殖户都很支持,也有一些时候,即使当地政府愿意提供帮助,大鲵养殖户也不愿意向他们展示自己最珍贵的“财产”,科学家们只能从普通大鲵身上获取蜕皮和口腔黏液作为遗传学研究材料。
野生大鲵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非经许可,严禁捕猎、经营和使用,但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人工繁育的子二代获得许可后可以经营利用。
针对法律,有学者曾提出质疑:人工饲养条件下的野生大鲵、人工繁育的子一代个体的法律地位该如何界定?
一些养殖户拍着胸脯坚称自己饲养的是“纯野生”大鲵。车静认为,“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很难区分哪些是野生的,哪些不是,只能根据遗传基因进行判断。”
根据基因检测,全国养殖场内有近80%的大鲵个体是“陕西种”。
在这项研究前,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多年来鼓励对大鲵增殖放流的做法,在车静看来缺乏科学指导,需要调整。根据2015年农业部公布的一项数据,此前10年累计向天然水域放流大鲵6万余尾。从未有人评估过它们被放流之后的成活率。
此外,长期习惯被人工养殖的动物,可能不适应立刻放流。车静说,“就像大熊猫,人工饲养了那么多年,要经过一段驯养野化,才能放到野外。”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许多大鲵养殖场建在保护区内,养殖大鲵一旦逃逸,或者在放流中存活下来,对本已濒危的本地大鲵种群来说可能造成巨大威胁。
“生物多样性不是靠美丽的生物组成的”
人工干预所带来的威胁,曾在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发生过。
日本大鲵1952年被列为“特别天然纪念物”。该国规定,所有的日本大鲵,包括人工繁育的后代,科研单位、博物馆和水族馆未经许可不许驯养,个人和企业不许饲养、运输和利用。
然而,当时人工引入的中国大鲵一度成为日本大鲵的噩梦。体型更大的中国大鲵与日本大鲵的杂交种优势突出,在野外放生后竞争力极强。杂交种让日本大鲵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放流杂交种的河中,基本上找不到日本大鲵的踪影。
这次,与中国大鲵至少分化为5个物种的研究结果同期发布的,还有伦敦动物学会负责撰写的论文《世界最大的两栖动物马上就要野外灭绝》。
论文披露,科考队走访的97个县里,有93个县没有找到野生大鲵。而在这93个县中,有74个县近年来已无人见过野生大鲵,18个县因有养殖场和有计划的放流而无法确定,只有一个县因为没有大鲵养殖场,才能确定有人目击到的是大鲵真正的野生个体。
论文作者之一、加拿大科学家罗伯特·墨菲指出,如果不改变相应的管理政策,中国大鲵将在未来10~20年真正变成一个单一物种。“这个庞然大物在我们的生态系统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无法预知它最终会走向何方。”
论文表示:“……政府支持的野生放殖活动并未促进大鲵的繁殖。在2015~2016年,我们发现一些大鲵在被放流后死去,即使侥幸存活下来,偷猎者也会威胁到它们长期的生存。”
不像大熊猫,大鲵没有乖巧的外貌。滑溜溜的黝黑色皮肤、没有眼睑的小眼睛,不太符合人类的主流审美。更何况,就像大多数两栖动物一样,大鲵隐匿在深山中。
“我完全理解,公众可能(认为大鲵)没有像熊猫、大象那样是举足轻重的。但其实生物都是公平的,生物多样性不是靠美丽的生物组成的,是靠各种各样的生物组成。”颜芳说。
野外考察动辄外出半年,但她并不觉得单调。让她遗憾的是,在初秋大鲵交配季,她从未见过大量在野外生活的大鲵。
车静相信仍有野生纯种大鲵的存在,它们也许在某个养殖场,也许在迁徙的车辆中。也许能够解开它们枷锁,让它们有机会重返自然的,就是更全面的基因鉴定普查。她建议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大鲵的追本溯源的工作,在全国开展细致的野外普查,同时调查养殖场里到底存在多少野生大鲵,禁止未经遗传核查的无序放流,不让大鲵不同物种相互影响。她还建议考虑针对目前发现的隐存物种,建立国家级繁育中心。
根据长期的野外调查,车静知道,中国大鲵至少一个隐存种可能已经灭绝。一只多年前在青海曲麻莱地区发现的大鲵,是该地区存在大鲵的物证,标本就保存在中科院西北高原研究所。这次调查时,他们驱车前往当年发现这只大鲵的河流。
河流依然奔腾,但无论如何努力,也难以找到这一支系大鲵的下落了。
【编辑:贾志强】 -
相关文章
- 热点新闻更多>>
-
- 这件事,习近平视为“根本大计”
- 习近平讲述“上合故事”
- 开启务实合作新局面
- 习近平这样论述“高质量发展”
- 习近平“上合声音” 引领上合发展美好未来
- 习近平为何把这个区域组织称为“典范”
- 经中央批准,共青团十八大将于近期召开
- 青春奉献母亲河 青山长绿水长清
- 金句!5年来,习近平这样说上合
- 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激励香港科学家
- 习近平强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 凝聚新时代青年力量
- 习近平为何坚信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必将成功?
- 总书记新时代科技强国动员令引发热烈反响
- 青年习近平的品格风范
- 团中央书记处同志参加“六一”少先队主题队日活动
- 习近平的足迹丨指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 习近平科技“新语”
- 习近平“上合声音”架起民心相通之桥
- 五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重要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