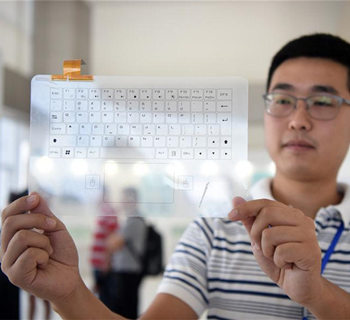老乡们纷纷转发的那篇文章叫《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源于山东省委书记节后的首场会议。省委书记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僵化、官本位严重、技术落后等问题,说的是全省大势,却也精确地戳中了这座老工厂的状态,裹挟着一介小人物的命运。
本文共10502字
预计阅读时间:27分钟
编辑 | 张 国
- 刷在墙上的时代背景 -
杨 海
记忆中,家乡的变化一直是缓慢的。今年不同,春节假期我第一次觉察到了这个中原小镇的明显变化。在肉眼可见的边边角角,那些不一样的景象总能提醒我,家乡真正与这个国家连接起来了。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GDP增长了40多倍,每座城市都辐射式地扩张,高楼成片地拔地而起。就连县城也早就变了样,开发区只用了10年就超过了老城区的面积,人气也逐渐积攒了起来。房地产开发商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城周边的几个村子消失不见,变成了一栋栋规整的高层住宅楼。
尽管外界正在经历空前高速的发展,家乡的样子还是没太多改变,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如此。
集市还是最早的十字街,没有延长,也没有拓宽。沿街的两层小楼贴着20多年前的白色瓷砖,楼下的批发部还习惯把商品堆在路边。就算20年不回家,再次归乡时人们依然能很快找到熟悉的店铺,除了老板变老了,商品换了牌子,其他几乎原样不动。
今年从市区回家的路上,经过那些熟悉的村庄时,满眼的白色闯进了视线:沿路房子的墙壁全都刷上了白漆,下面画上砖墙的图案用来装饰。上百公里的路上,十几个村子整齐划一。在我的印象中,家乡的村庄是单调,甚至粗糙的。从我记事起,农村的法则就是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盖房不太讲究外观,墙往外多挪一寸,比在上面刷一层漆重要得多。所以家乡农村的房子,外墙大多是直接裸露的红砖,讲究一点的人家会抹上一层水泥,再没别的装饰。
当然,白墙不会是村民刷的,这是“美丽乡村”工程的一部分。效果也显而易见,从车上一路扫过,村子看起来确实比之前整洁不少。只不过再往里走,穿过沿路的房子,白墙就不见了。村庄又恢复了冰冷的灰色,就像冬季的树皮、老乡们的脸色。
家乡也多了很多的户外广告牌,立在村口、路口。墙上的标语也换了样式,此前的标语大部分是简单的蓝字,千篇一律。现在不但加上了白色背景色,有的还会给字体描边。字体颜色也比之前丰富,除了常见的蓝色,红色、黄色的标语也开始出现。
标语口号的内容也比之前统一不少。很长一段时间内,家乡的墙体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计划生育、家电下乡、婚纱摄影、祖传老中医……现在,不管是户外广告牌,还是墙体广告,内容几乎全是“坚决打赢扶贫攻坚战”或者“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进了样式、增加了投放密度后,这两项政策确实能让人印象深刻。
这两个口号几乎涵盖了家乡政府工作的全部内容。“美丽乡村”就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部分,除了刷白墙,农村环境治理也走出了政府工作计划书。
农村环境问题主要是固体垃圾污染。在以往,每次逢集,街边就能多出几十个垃圾堆。两三个镇里的“城管”会开着三轮车把垃圾收集起来,再倾倒在街头的一处干沟里,没有填埋,更没有分类。小规模的垃圾堆直接就地焚烧,每到傍晚街上就会飘荡着一股塑料熔化的味道。
村里的环境同样糟糕,池塘上面漂满了塑料废品,动物尸体和剩菜剩饭也都往里面倒,夏天时靠近池塘就能闻到一股臭味。就连田地里也随处可见废弃的瓶瓶罐罐,一些被农药毒死的鸟类尸体腐烂发臭。
今年,镇上多了很多垃圾桶,甚至出现了一辆垃圾压缩车。年关最热闹的几次逢集,总能见到几个穿着荧光服的老大爷抽着烟,围成一圈,把一米多高的垃圾堆搬到车上。离镇子两公里的地方新修了一个垃圾中转站,垃圾车把垃圾放在那里,再由县里来的车转运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垃圾桶也第一次出现在了村里,两三户人家共用一个。各村也都派人把池塘清了一遍,只不过积攒了几十年的垃圾本来就很难打捞干净,年关几天,新垃圾又重新入坑,池塘的变化并不明显。
明显的是家乡的那条小河,上世纪90年代时,河水还很清澈,里面有几处芦苇荡。小孩子喜欢往里面扔砖块,总能激起一群飞鸟,和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后来有人在桥下修了水坝,截出一段河段养鱼,河水也因此变成了死水,开始发黑变臭,芦苇荡也消失不见。水质变差后,养鱼场也很快废弃,但水坝却没人处理,任凭河水断流,淤泥阻塞。
今年镇政府拿出7万元钱,雇人把桥下水坝拆了,疏通了那片堵塞区域。只过了半年,河水就清澈了许多,不知从哪里生出几群野鸭整天在河面上游荡。
可不知什么原因,年前还算清澈的河水,过完年就生出了“赤潮”。镇上那几个“环卫工”也不见了,他们说自己是镇政府临时雇来的,只管年关几天,“一共500块钱”。
扶贫工程同样热闹。乡亲们除了种地,就是外出打工,没有什么产业。这次回家,感觉产业一下多了起来。沿着公路随便走一走,就能在空旷的田野里看到那些显眼的“产业基地”。这些基地一般都处在村子边缘,有两个篮球场大小,统一采用钢架结构,高度接近两层楼。
农业区忽然长出这些庞大的“工厂”,多少让人觉得有些突兀。但这些都是“产业扶贫项目”,每个村都有一个,有些项目是搞养殖,有些搞农副产品加工。不过劳动力都长期在外打工,这些“基地”一时招不来人,大部分还处于空置状态。
靠近集市有个“巧媳妇”产业扶贫基地。村支书介绍说,这个基地切合家乡男人都不在家的实际情况,为留守妇女提供了一个在家门口工作创收的机会,“在里面做手工笤帚”。
附近的老乡说,“巧媳妇”基地确实开过两次工,村里很多妇女都去了,因为“去一次发50块钱”。两次开工时间也很巧,都刚好赶上了上级检查。
今年1月份,家乡下了场10多年未见的大雪。“巧媳妇”基地禁不住积雪的重量,塌了。
- 花骨朵里变迁的审美 -
玄增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家每年过年前都要去一趟花市。
花市在郊区,挨着崂山。从花市外看冬天的北方,天高野旷,木石嶙嶙。可一进门就换了季节,人人都把厚重的羽绒服搭在臂上,在温热的大棚里走两今年花市人格外多,人们像买菜一样围着杜鹃花、茶花、仙客来。过年要讨个喜庆,大红、桃红、粉红的花格外好卖。卖花的人甚至把橘子树栽在盆里,近两米高的树上缀满了黄澄澄的小橘子,如同圣诞树。枝细花大的蝴蝶兰一排排地立在船形的花盆里,花枝用火红的带子围着,在正面打了个蝴蝶结。
花的名字更是直白:金玉满堂、黄金万两、一帆风顺,也不知是谁给起的,仿佛来年的红火日子都藏在这花里了。

视觉中国供图
家里老人都爱看花、养花,尤其是我姥爷。在姥爷家,花的好看程度是以电视机为中心向四周递减的,高高低低的花骨朵拥在电视机的两侧——那里通常是老人们视线聚焦的地方。阳台的角落也挤满了红的绿的,粗略一数,姥爷家的花超过30株。
姥爷把这些花当宝贝一样养着。花就像小孩子,不同的花有不同的养法,有的要一周浇两次,有的两周浇一次,还有的一个月浇一次就行。姥爷八十多岁了,有时会忘了在菜里放盐,却从来没忘了给花浇水。今年爸妈和我从花市搬了一盆君子兰回去,肥厚的叶子向两边弯着,淡橙色的花苞从中间冒出来,看样子快要开了。
“哎呀,怎么又买花!”姥姥头发雪白,一笑眼睛就眯成一条缝,指着那一堆一堆的花花绿绿,“你看看,家里都快放不下了!”姥爷向来话少,只是弯下腰端详:“嗯,这花长得一般,以后少买点。”然后低着头,把它慢慢挪动到距离电视最近的位置。
听说以前的花市没这么多花,也没这么多人。几盆花用塑料薄膜一盖,就是一个摊位。过年期间,比起买真花,人们更喜欢买礼花和鞭炮。火一点,往天上噼里啪啦一炸,热闹来得更实在。第二天清早出门拜年,踩着满地的红色碎纸,也像走在花海里。
几十年前,纯粹的“好看”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老家人都还在用脸盆洗热水澡,靠蒲扇撑过夏天,所有的“好看”也必须拥有它的实际功用。每户人家里为数不多的装饰恐怕就是墙上的月份牌,以及铺在新买的冰箱、沙发、电视机上防尘的白色镂空布料。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用处。
可姥姥那时还是会在路边采一把野花,插在喝空的牛奶瓶里。姥爷也会托人弄来几盆小小的杜鹃,放在土炕边的桌上,那也只是极偶尔的时候。每个个体如同他们所在的集体一样,反对“华而不实”,甚至反对“好看”本身。
姥爷姥姥都是老实人,从来没有张扬地“好看”过。姥姥年轻时个高腿长,觉得恋爱是件羞耻的事,会跟上门说媒的人生气。27岁时才由人说媒遇见了姥爷,在那会儿已经算是“大龄剩女”。
姥爷也是个实际的人,见过姥姥后没隔几天,就骑了辆“大金鹿”自行车来到姥姥家门口:“你看咱俩这事儿行不行?”其实姥爷姥姥都是“好看”的人,可那会儿没人愿意承认自己在意这一点。姥姥觉得这人“实在”,就同意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日子都过得清苦,连“实际”都顾不上了。姥爷在“文革”中被批斗,戴块牌子站在台上任人辱骂。闹饥荒时家里顿顿野菜,裹着面糊,熬成稀粥。在那个时代,花和果都不能要了。
我以前不明白姥爷姥姥为什么喜欢大红大绿的花草,觉得俗气,后来才懂了,那是苦日子过够了,想多看看喜庆的颜色。
老家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花市,花在以前是像玉石古玩一般的珍稀品。如今,花市高大的玻璃温室有上千平方米,满地的花像蔬菜水果一样寻常。人们仿佛已经把苦难甩在身后,可以大大方方地追求纯粹的美,什么都不为的美。挂灯笼只是因为喜庆,买花只是因为好看。
前些年,花市不叫花市了,改叫“花卉交易中心”。在这个时代,美也是可以被消费的。一位摊主把桃红色的杜鹃花一盆一盆摆出来,花叶簌簌抖动。“我们可不像你们把花看得那么娇贵,”他是个高大的北方男人,粗手粗脚,口气像是在教育人,“在我们眼里,这些只是商品。”杜鹃100块钱一盆,君子兰160块钱一盆。
家是一切商品的属性终结地。每年过年,除了我和爸妈要给老人们买花,姥爷也会亲手栽一盆水仙给我们送来。我至今不知道那水仙的花苗从哪里来,也从没问过,只把它当作一个不知来由的传统接受着。水仙花期有限,我们也把它摆在电视旁边,花一开就是满屋子香气。
过完年,爸妈跟我一起来了北京,看到我这里没花,非要出门买几盆,然后反复叮嘱,什么花要两周浇一次,什么花要每月浇一次。我有些佩服姥爷,可以把每种花的浇水时间记得那么清楚。
- 一大家子“落后产能” -
程盟超
春节假期末尾,老爸在微信朋友圈里默默分享了一篇文章,这已是年过五旬的他近年来少有的情绪表达。
老乡们纷纷转发的那篇文章叫《山东终于意识到自己落后了》,源于山东省委书记节后的首场会议。会议上讲了很多问题,甚至用“尴尬”“破釜沉舟”之类的词,形容山东当下的经济形势。
父亲和我的祖父祖母,两代三口人,都在山东小县城一个历史追溯到1949年前的农用发动机厂工作。省委书记开诚布公地谈思想僵化、官本位严重、技术落后等问题,说的是全省大势,却也精确地戳中了这座老工厂的状态,裹挟着他一介小人物的命运。
家里长辈对厂子无疑有认同感。我的童年记忆被意气风发从事销售的父亲跑过的各大省份串联起来,有时和父亲从外地带回的客户吃饭,满席都是他们对这座大厂的赞美。在祖母的回忆里,这座厂子有干不完的活儿。工人们每天两班倒,忙起来没有人顾得上午饭。至于“战高温、夺高产”“九月会战”,更是激扬人心的集体回忆。
到我父母那代,这种荣耀感似乎“功利”了一些。据说上世纪90年代,工厂里最普通工人的年收入都能轻松破万。在“包分配”的最后年代,班级里的前几名才能进入工厂,成绩相对一般的会被分配到交警系统。
“人的命,天注定。”我妈如今如此评价。她不积极的态度来自于这座工厂目前的状态——工人们依旧拿着20年前的千元月薪,大部分每天只有半天班可上。工厂人数从巅峰时的5000削减到现在的2000多,其余都遭“社会分流”。老爸在厂里奋斗了30年,如今挂着“中层”的头衔,月工资也不过3000多元。
和长辈一番长谈后,我能为这座工厂的衰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采取了错误的发展战略,始终主打中低端柴油机,错过了上线整车产品和中高端环保产品的好时机;再比如越来越多的技术人才流失,人们纷纷前往大城市谋生。
坦白讲,这场衰败里有着鸡毛蒜皮般的人为因素,也存在一些相对难以改变的力量。一如父亲所说的,厂里对工人所施行的“计件制”很难调动起人的积极性,销售人员更是“吃大锅饭”,业绩好坏收入基本一样。历史的倒影过长地留存在这个工厂,显然并不是一两个人的过错,而是一种集体的僵化。
再看看我的家乡,一座毫不起眼的县城,如今被列为贫困县,在周边市县里以“道路破烂”闻名,每平方米的房价却仍是一个熟练工人月收入的三倍五倍甚至更多。年轻人在这里的娱乐方式,除了逛超市、看电影,也就只有泡网吧——毕竟,我们甚至没有像样的商场和咖啡厅。我的母校,县城最好的高中,曾经在省里富有声望的“名校”,也已经很多年没有培养出清华北大的学生。我的高中班主任春节时告诉我,县里经济不乐观,优秀的师资和生源都在被体面的地级市挖走。
在这样的形势下,纵使老工厂已然尽力开出富有诚意的工资,依旧难以留住技术人才。按照父亲的描述,年轻人会在厂里短暂地停留两三年,学成技术后就飞向远方。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个县城只能作为跳板。
“2012年,市面上还有75%的农用机械在用柴油机,两年过去,只有不到25%了。”按照父亲的想法,没有了体制和技术的优势,衰退早晚会来,但他并没想到改变会来得如此之快。如今,环保的压力终于切切实实地压在了这座年迈的工厂身上,诸多配套厂环评不过关,遭遇限制生产;又因为产品太过低端,实在没有利润去引进新的环保设备——最终,工厂开始陷入已有订单都难以完成的境地。
摒除感情来讲,低端产能被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两只手合力扼死是没什么问题的。但令我深思的是,在这小城乃至其他不起眼却广阔的地方,恐怕有不少工厂、不少人面临产业迭代的夹心境地。
就像我家楼下70后的两口子,丈夫在我父亲的工厂上班,月入千余元,妻子所在的化肥厂,据说前几年已经倒闭。他们如今有上小学的孩子,家里背着车贷和房贷,很大程度上靠父母接济。再比如我妈的一些朋友,尽管已经熬到退休,可因为企业效益太差,只能发下千元的退休金,不得不再出去谋一份职业。
我并不会因此过分悲观。将落后的产业淘汰是必然的趋势,身处其中的人遭遇裹挟也只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我也不会自大地得出什么“中年哀伤”“县城凋敝”之类的结论,看看楼下的两口子,一个开始兼职算命,另外一个做起了微商和美容生意。最普通的小人物总会尽力活下去,他们或许不需要怜悯。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改革提上重要日程后,我也并不知道这个伴随我长大,如今已成为落后产能的老工厂,是会凤凰涅槃,还是永远沉寂下去。普通人的命运难免随着大势流动,但能看清潮流方向的,终归是极少数人。在这一年又一年的爆竹声中,我目前唯一能清晰感受到的,是时代变迁带来的物是人非,以及历史长河中夹杂的不确定和无力感。
- 是空空荡荡 却嗡嗡作响 -
胡 宁
近十年里,这座东北四线城市曾在全国人民面前出过两次镜,只可惜都不是什么好事。一次是钢厂股权调整时闹出了人命,还有一次是被命名为“8·13北京三里屯砍人案”的著名案件,凶手是我的老乡。
其他时候,这里从未威名远播过。当地的火车能明白地显示出这里的生存节奏,K字头是这里最快的火车。有关高铁和动车的传说,如同许多当地经济提速的计划一样只闻其声。人们依旧以恒定的步子朝着不知道是不是时代方向的方向挪动着。除了生活,他们能做的并不多。
这些错综复杂的情绪在家乡的钢厂身上算是做了集合。钢厂最盛时有员工3万人,有自己全套的社会体系,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学校系统、医院、图书馆、大型商业广场、住宅区,近十万人的生活围着它转。钢厂所属的区距离市中心较远,但是一度让“市里”的人都向往着成为它的员工。钢厂人会骄傲地说,没有这个厂,就没有这个区。
上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在很多类似的工厂掀起“下岗潮”时,这家钢厂虽也改制,但是仍在享受着它最后的好时光。据钢厂的老员工说,一位总工程师提出上更先进的设备。这个提议事后看起来十分明智。这位总工程师嗅到了各大钢厂“上规模”的先机。只是可惜,当时的总经理否决了这个提议。
进入21世纪,一家民营企业布局收购和重组钢厂时,引爆了群体情绪。这家企业的总经理葬身于此。这件事引起过轩然大波,据说还被一些学者用来论述私营经济的“原罪”,并引发了关于捍卫国有经济的讨论。这次事件留下了许多谜题,比如民营企业是否与官员合谋变卖国有资产,血案是谁在背后做了推手,那些声称民营企业会让钢厂职工全都下岗的传言又是怎样发酵的。
那家民营企业在事发当天就用大喇叭宣布,永不进入这家钢厂。如今,同一个喇叭每天都念诵着厂内的日常事务。在高炉和密布的楼房里,还回荡着大机器时代垂垂老矣的轰鸣声。绕着这家钢厂,走上一圈还是要两个小时。但是它看起来是如此渺小落魄。
按照老员工的话说,这几年,厂里能走的人早走了。祖孙几代人都在钢厂效力的情况依然普遍,但是,能不来的,也都不来了。老人对这家钢厂充满感情,但这份感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于对黄金年代的美好回忆。
钢铁行业起起落落,但是这家钢厂命运多舛。在反腐败的高压之下,近几年有两位厂长自杀了。那些学校、医院、商场早就在21世纪的头一个10年里被剥离。如今,钢厂的员工不足5000人。随着钢厂瘦身,还会进一步减少。最近几年,听说连本市医院里当临时工的小护士,都瞧不上钢厂人的工作了。
近两年,市里的人一窝蜂地在另一区域掀起了买房热潮。钢厂离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区域越发远了。当我在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里站在山头望着这家钢厂的全貌时,想起了李宗盛的那句歌词:“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你可以为钢厂的衰落找上许多理由,也可以模仿网上的论调,大谈东北的“落后”。
钢厂某种程度上说是地区的缩影。“共和国的长子”的确落寞了。但是不知道从何时起,菲薄落寞的人,再使劲儿泼盆脏水,成了很多键盘侠的爱好。他们甚至能堂而皇之地喷出难听的语句,丝毫不感到有任何不妥。
走过家乡街头的时候,看到空空如也的创业中心我会忍不住笑,其中有点自嘲,有点悲凉。创业中心旁边是一片有名的菜市场。过年了,那里熙熙攘攘。再过一道桥,一片新区在崛起。只不过那里与创新创业无关,都是围绕着住宅和商区建设的。看到这些,我心里觉得释然不少。尽管这里无法在时代的风口成为弄潮儿,但是在生活里,这里的人也没落下。他们努力工作,努力休闲,事实上,他们从没有比其他地区的人多一分或少一分什么。面对生活,大家都一样。
过年期间读到的几篇文章让我觉得可笑。比如流传甚广的“东北没有互联网”,这里的确没有大型互联网企业,但是最新的互联网产品也已在每个人的手机里。互联网正结合这座不大的城市、不怎么密集的人口的实情,发育出它该有的样子。只要是一个稍有智力的人,都不会傻傻地以一个国家的首都或经济中心当作参照系,再来把这座小城黑得体无完肤吧?至于有人说,网络主播一半是东北人,这句话背后蕴藏的蠢劲儿我已经懒得指出。
我无非是想呼唤些许善意,在2018年伊始。因为无论是这家钢厂,这座小城,或是东北的兴衰起伏,都只是时代作出选择之后的结果罢了。那是无法抗拒的、杂糅了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东西,随口说容易,说清楚却难。谁也不知道下次它会如何选择。谁也不知道今天风光的CBD是否有一天也会如同钢厂。不必急着赞同或反驳。无论时代的风向如何变换,努力生活的人值得被给予善意和尊重。他们左右不了什么,除了柴米油盐。
- 既没有跌 也没有涨 -
江 山
当我提出想去当地一个售楼中心“看一下”时,母亲以不可置信的语气反问:“你还想要买房子?”
经历了去年一场从浙江到江西的千里奔波后,她对于买房这件事早已“敬谢不敏”了。
那场买房的“风暴”起于去年3月北京出台限购新政策的“青萍之末”。每天守着电视看新闻的父母,也坐看全国各地楼市的躁动不安。
这一苗头早已显现。就在我们居住的浙江小城嘉善,因为有着毗邻上海的地理优势,房价也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翻了两番,每平方米从四五千元直逼1.5万元,甚至比所属的地级市嘉兴的房价还要高。
当几年前高铁开通,来往上海的时间缩短至20分钟时,我们尚未预料到变化会如此快速地发生。最初,许多本地人乘着高铁去上海上班;再后来,一些在上海买不起房的外地人退而求其次来此定居;最近一种新潮流是,上海老人把房子留给儿女,纷纷来此处买房安享晚年。
“都是上海人炒高了房价”,不止一个人在抱怨,可好像受害者也不止当地人。高铁上的一位上海籍阿姨,心有余悸地对我这个陌生人说:“还好我买得早,不然现在都买不起了。”
“什么最升值?当然是房子了。” 当我把这些事当作家乡轶闻来讲,单位一位和父母年龄相近的同事听了却告诉我。因为对楼市有着长达数十年的观察和实践,她已经购置了好几套房子,成为了我们心目中“隐形的富豪”。
“在北京要买靠近中心的老房子,但在家一定要买新房子。”作为过来人,她劝我不要让父母的存款放在银行贬值,“用在刀刃上”。
说得我有些心慌,打电话回去,责怪父母思想老旧,没有把握住时机。还照搬一个段子跟他们开玩笑说:“如果能穿越回过去,我一定要劝你们宁可贷款也要多买几套房子。”
母亲听了,也有些后悔莫及。两年前,她曾跟着同事交过定金,但是被极度风险规避者父亲制止了。她如今有些嗔怪地对我说:“如果你当时回家工作,不就买上了吗?”
不敢轻易买房的背后,他们更深的焦虑是养老问题。对于老家在江西、工作在浙江的他们而言,退休后是去是留,尚未可知。当然,他们还有一个在我看来更不切实际的愿望——在北京买套房养老。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思想里,跟在儿女身边才足够安全。
好在确认“钱存在银行里只会贬值”的共识后,终于,母亲说动了父亲,因为想着江西房价还有更多上涨空间,决定去赣州看看房子。得知我们要回老家买房,亲戚们倒是兴奋,但也面露难色地说:“很多人都赚到钱回家买房,这里现在也在限购,能买的房子不多啦。不如带你们去几个外围的楼盘看看吧。”
去的第一个楼盘,号称“城市山谷人文院墅”,坐落在一座远离市区的山岙里。
我们和另外几户人家看完沙盘,坐上一辆电瓶车,沿着唯一一条修好的路上山。两旁是裸露的红土,刚刚运到的大树四仰八叉地倒在路边,还没栽进坑里。
开到一处凸起的高地,导购让我们下车,指着山脚下几个正方形大坑,自信地说,这是几期几期工程,“已经打好地基了”。
这时,有人指着不远处一栋三四层的自建小楼,问“这栋楼会不会挡光”。得到的回答是,“这户人家现在还未搬走,未来我们一定会谈好的。”语气轻松得仿佛像赶走一只苍蝇。
我小声地对母亲说,“别墅区都在山里,高层建在靠外围的公路旁,一定是为了挡噪音”。不料声音竟大了点,惊动了导购,她剜了我一眼,不作一声,却让我觉得心虚。
第二个楼盘相对让人觉得靠谱了许多,只打出了“江景房”和“精装修”的口号,单价比之前的那个楼盘贵了一两千。看样板房需要排队,100多平方米的家挤满了手牵着手的情侣、带着小孩的夫妻以及牵着狗的家庭。
我和母亲都对这个楼盘感到满意,但是导购领着我们到一块大牌子前,指着上面一堆表格说,“你们是外地人要注意一下限购范围,到时候拿号、开盘可以托人,但确认付款时需要本人到现场亲自确认”。再坐12个小时火车的旅途让母亲感到为难,可也不得不遵循这样一套流程。
回到浙江,她要购房的意图不知如何泄漏出去,被人介绍去本县新楼盘看房。尽管价格比江西的房价高出很多,但是导购不失时机地告诉她,“看在私人关系上,会给你一个优惠价格”,让她动了心。
这一次母亲终于准备出手了。光是把家中分散的积蓄取出,她就跑了一天,但是到了开盘那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
她气得声音都有些抖,“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原来就差临门一脚时,对方告诉她,只有全额付款才能享受优惠。她觉得受到了欺骗,要求退还之前打的5万元定金,却被对方告知不能退还。
我打电话给销售方,谴责他们不讲诚信。对方答应退还,却也不甘心地补充了一句,“我们看到两位老人也很犹豫,如今这房价肯定会继续涨,有时候还是要狠得下心。”
可是母亲早已疲于奔命,更害怕应付未来更多的变故,放弃了所有的买房计划,偃旗息鼓。她唉声叹气地说:“我们没有这个命,还是老老实实存钱,等着到时候你定下来了,在北京买一套。”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今年春节,买房仍是我们饭桌上的谈资:楼下一套空置许久的房子终于搬进了新的住户,但互相见面也不怎么打招呼,连姓什么都不知道;前几个月,父母帮一位退休老同事卖掉了房子,“又是上海人买的”;而一家伯伯却悄悄卖掉了自己住了大半辈子的房子,搬到上海早就买好的房子里,照顾在那里工作的儿子。
我突然觉得,钱钟书先生早就在70年前出版的《围城》里勘破了这层道理,“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进来”。只是在这一退一进中,没有多少资本好搏的我们就成了陪客和路人。
前几日,我们一家三口去了当地一个新修的公园游玩,远处就是那个楼盘。在白得晃眼的阳光照射下,新盖的高楼影影绰绰,背后衬托着的天空蓝得有些虚假,真像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那块巨大的幕布。
唯一让人安慰的是,这个楼盘既没有跌,但也没有涨。
--------------------
原标题:《我恨假期太短 只够看你一眼》
原文刊载于《中国青年报》(2018年02月28日 9版)
———
本文为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未经授权不得使用。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需授权,请长按或扫描下方二维码

欢迎给冰点(微信号:bingdianweekly)留言发表你的意见
微信值班编辑:秦珍子 吴蕴聪
-
相关文章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热点新闻更多>>
-
- [ 03-01 ]
- [ 02-28 ]
- [ 03-01 ]
- [ 03-01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
- [ 02-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