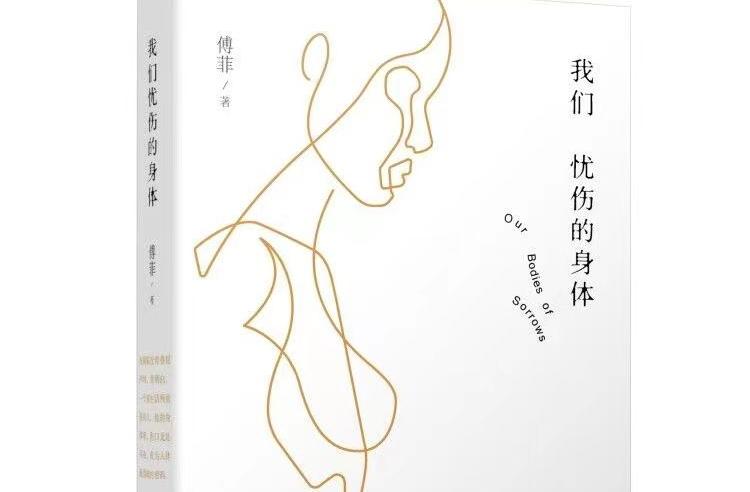夜读|自称“社恐”的年轻人,进了邻居群
在这一段上海封控期中,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邻居的名字。
像所有人一样,我们小区早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邻居群,但互相之间还是宛如陌生人一样,除了孩子的玩伴,不说在线下没有交往,连名字都不知道。在群里万一有沟通的必要,往往都是这样的:“603的邻居您好,我是503的,您家小孩的声音能不能小一些?”
更不要说,很多以“社恐”自居的年轻人,连邻居群都不屑于进,有事进群,无事退群。
在以往,上海人喜欢将这种邻居间的陌生感整合进一种更宏大的城市叙事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每个家庭关上门都是一个世界。
这当然说得没错,相比前现代的“熟人社会”,现代城市文明本就是一种“陌生人社会”,陌生人之间的以礼相待与互不干扰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随着“宅文化”的兴起,“陌生人社会”的说法被推向极致,“社恐”成为了一种时尚,同事、同学,特别是邻居之间的冷漠被视作一种新的政治正确。以至于,没有人情味成为了上海这样大城市的“城设”之一。
但在这次疫情中,至少在邻居的层面上,大城市人“没有人情味”的说法可能要被证伪了。
无论是小区团购,还是邻居间的互助,在这段时间成为了上海人在封控中的暖意来源。
这几周,我大概加了十几个邻居的微信,也知道了很多人的名字,包括一些家长里短:谁家人口特别多,谁家喜欢吃啥,谁家老公搬货时力气特别大……
我这几天甚至觉得,对于一个社区的融洽度而言,有一些家长里短可能也是必要的,至少说明互相之间“有兴趣了解对方”,也是一种邻里亲密度的象征。这与现代人的边界感和分寸感未必天然对立。
所谓共同体,除了共同的荣辱感之外,有互相了解的欲望可能也是共同体可以维系的前提之一。
我昨晚睡前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最近看得最多的群竟然是几个各具功能的邻居群。这让我有些震惊,我可是自诩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啊:不仅是潜水,我竟然还经常发言;不仅是在团购问题上发言,小区群在这段时间出现了各种公共议题,我经常自以为高明地“这个问题我来说几点”,试图给出几点“指导意见”。
但发言的“代价”是,当我和老婆在饭桌上拿这最近掌握的邻居八卦来调侃时——这是封控期间为数不多的快乐来源,我是一个所谓作家的“秘密”也被邻居知道了,成为了邻居调侃的对象。
前两天,一个团长在发表“团购感言”时,专门爱特我感谢了我的“仗义执言”,我一下就兴奋地拿着手机向老婆炫耀,“你看到了么”,兴奋程度堪比我的新书被某位师长表扬了。
我竟然就这样成为了一名沉溺于小区群的知识分子,我不是应该去关心天下大事,关心国际局势么?
但很可惜,都这样上蹿下跳了,我还是没能成为一名小区的KOL(意见领袖),我倾心佩服的团长们才是。
继断舍离之后,来一个源自日本的亚文化——宅文化,在封控期间的上海也遭到了某种意义的颠覆。
这段时间,可能每个小区都有几个突然露头求助的宅男。很多宅男在家里囤了各种方便食品,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握,快乐地与电脑度过了一周之后,才发现没吃的了,然后才人生第一次加入了他们这辈子以为都不会加入的邻居群,一加入就“缺乏社交技巧”但一点也不矫情地求助。他们的诉求往往是:有没有不需要进厨房,直接可以吃的东西?
让我没想到的是,据说宅男们的求助信息往往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很多女性(以老阿姨为主)纷纷献出爱心,甚至把物资送到门口。
在这样一种奇妙的场域里,“宅文化”竟然就被“邻里文化”果断收编了,没有任何传说中的“文明冲突”。
这让我想到,现代城市文明除了边界感之外,不同人群之间的共容、合作与理解同样重要。甚至,边界感的成立也是建立在此种理解之上的。
城市不应该是一个原子社会,但他可以容纳那种不想与其他原子交往的原子。
项飚在《十三邀》里曾对对许知远感叹“附近”的消失。他说:“个人的意义与尊严的出路不在于个人,一定在于关系。没有一个天然的个人尊严,没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你一定要建构出附近,重新去想这个关系,建构出关系。”
这段话我并不尽然同意,但在我们今天谈论的话题范畴中,“附近”的意义在与于,提醒我们重新思考和界定个人与邻居,城市文明与邻里关系的关系。
在这段时间,上海人不都在“建构附近”么?
现代城市文明、宅文化、邻里关系,并非如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互不相容,人情味也未必是前现代社会的“遗存”,这次经历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邻居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连接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既不是前现代整日家长里短的“熟人社会”,也不是所谓的冷漠现代都市。
上海疫情消散之后,邻居群和邻里关系自然不会再有这段“非常时期”这么热络,但我知道了“你的名字”,也知道了邻里关系所蕴含的巨大可能性:这是一种深具弹性的关系,不必在任何时候都以亲密示人,但在需要的时候,它还可以像这次疫情中一样发光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