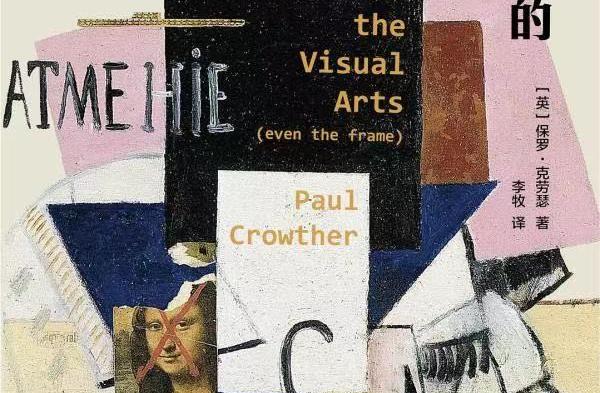为什么要写一本诗化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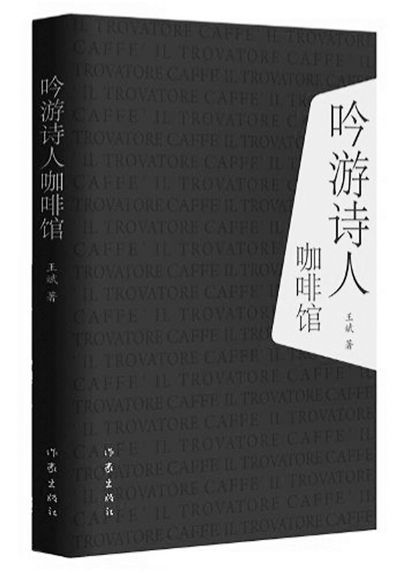

月光走了,她没有再回头。萧朗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发着呆,如同经历了一场似真非真的梦境,被一股突如其来的悲伤淹没了。
萧朗百感交集。
在小说《游吟诗人咖啡馆》的最后,王斌用这种方式结局。月光始终是一个谜,似乎是真实人物,又似乎是一次幻觉。
可能很少有人能读完这本小说吧。毕竟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将萧朗、远乔、娇娇这些人凑齐——他们都不食人间烟火,关注灵魂多于关注生计,却能在都市中体面地活着,还能在咖啡馆肆意浪费时间。
对萧朗式的生活,王斌是熟悉的。过去15年,他一直如此,写了7本小说,很少被人关注,在《游吟诗人咖啡馆》结尾,他署上“于北京博雅居”,但“博雅居”是远远谈不上“博”的蜗居,从它到其他地方,王斌经常要挤公交车。
萧朗、远乔这种文青还值得关注吗?这么少的故事量,如何能撑起一部长篇小说?在充满误会、缺乏诗意的现代都市中,为何要写一本诗化小说呢?
确实,《游吟诗人咖啡馆》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安德烈·纪德的《田园交响曲》,或者是约翰·班维尔的小说,但王斌的目光更远。所谓游吟诗人,是兴盛于11世纪至13世纪末的游唱诗人,他们将十字军的尚武精神与骑士风度融合在音乐中,他们不是流浪汉,大多出身于贵族,他们咏唱,只为挽留一份正在消逝的精神之贵。
王斌要用《游吟诗人咖啡馆》来宣告:“中国小说亟待找到回家的路。”
到图书馆工作,改变了我的命运
北青艺评:在您身上,有很多标签,如青年批评家、编剧、小说家等,还参过军、干过漂染工、当过图书管理员,曾与张艺谋多次合作,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王斌:我生在福州,8岁时随父母到了江西南昌,上中学时,不喜欢数理化,考不上学,整天坐在教室里索然无味,就自己读书。15岁时,我当兵去了福建,20岁退伍,回到南昌。先后在漂染厂、内衣厂、无线电装配厂当工人。
1976年后,社会回归正轨,感觉终于冲出雾霾,看到了阳光。那一阵子,我每天都在读书,和一些回城的老知青聊天。每天从江西省图书馆门口经过,但自惭形秽,一直不敢进去。
一天在路上,听到有人喊我名字,从侧脸看,是我的小学同学,他当时正上大学,已经快毕业了。想到自己只是个工人,感到很自卑,所以我装没听见,骑车就跑。他喊声越大,我骑得越快。最后,他还是追上了我。他知道我从小爱读书,而他的妈妈正在省图书馆负责,闲聊中,他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工作。
我当然愿意了。第二天,他就带我去见他母亲,他母亲和我聊完后,评价还好,就把我调到了省图书馆,这是我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图书馆工作期间,我写了一篇文学评论,评黑马文学的,投给《人民日报》,据说引起编辑部内部争论,不少编辑认为文章的思想倾向有问题,不应发表,感谢当时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老师,他力荐此文。
在报社安排下,我到了北京,用一个通宵的时间把文章改完,然后就坐火车回南昌了,还没到南昌,稿就发表了。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在当时南昌可是件大事,那么多大学教授都做不到,一下就轰动了。这是我的第一块敲门砖。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文坛上算是有了一点知名度,和孙甘露、莫言他们都有往来。
与张艺谋的合作,纯属偶然
北青艺评:您又是如何与张艺谋合作的呢?
王斌:我离开江西省图书馆后,去了河北,在《文论报》(后改名《青年评论家》)干了一段时间,不久后离开。青年电影制片厂知道后,把我借调了过去。
1989年6月12日,作家刘恒给我打电话,说新片《菊豆》的讨论会,能不能参与一下?我说上午有事,下午一定去。所谓“上午有事”,因为评论家李陀飞美国,我得去机场送他。送走李陀后,我赶了过去,张艺谋作为导演也在场。在会上,我提了一些具体意见,谈完就散了。此后去张艺谋的剧组探过班,和他吃过饭,但彼此交流很少,更没提过合作的事。
突然有一天,张艺谋不经意地对我说,能不能把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我立刻说行。当时我辞职了,没工作,正想找点活儿干。那本小说就是王朔的《我是你爸爸》,姜文也在场,张艺谋认为,只有姜文能演这部戏的主角。
剧本改好后,姜文临时有事,演不了了,张艺谋便把本子给放弃了。可剧组已搭好班子,不能说撤就撤啊,张艺谋问我,还有什么可拍的吗?我此前多次向他推荐余华,当时推荐的是另一篇小说,张艺谋觉得还好,让我去和余华联系。
在余华家,我问他有什么最新作品,恰好当时《收获》准备刊发他的新作,他正在看清样。我问余华:“这个能拍电影吗?”他说:“拍不了。”这就是后来的《活着》。
只看小说文本,确实拍不了,但张艺谋就有这个格局,包括《红高粱》,只看文本,也是拍不成电影的。可以说,没有张艺谋,就没有电影《活着》,所以在最终署名时,第一编剧是张艺谋,第二编剧是全体主创。
对于电影《活着》的拍摄过程,后来出现了很多种说法,但我是当事人。
从那时开始,我和张艺谋合作了16年,即1990年到2006年,我先后写过《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剧本,策划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影片。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出现了观念差异。
北青艺评:您说的观念差异,具体指什么?
王斌:不说大家也知道,从《英雄》开始,拉开了中国商业大片的大幕,从业人员收入倍增,但曾经的氛围改变了。拍完《满城尽带黄金甲》后,看片会上,我一开始什么也不想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一个曾拍出《红高粱》《活着》的导演,怎么会拍出这样的影片?不应该反思吗?
我觉得再说下去,就要伤感情了,毕竟十多年的朋友,不能因为观念差异,影响友谊,所以我就淡出了张艺谋的团队。
故事量少,是为了挑选读者
北青艺评:电影编剧的收入应该比较高吧?自己放弃了,不觉得可惜吗?
王斌:首先,您说收入高,那是后来的事,别看我编了那么多剧本,得到的稿酬很少。其次,我从少年时便想当作家,有了一点空间和自由后,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去读书和写作。我这个人对生活要求不高,不是特殊情况不打车,吃饭只去最便宜的餐厅,我不想“卖惨”,不想说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总之大大低于你的想象。
我可能是最早一批自由撰稿人,从2006年到现在,我已出版11本书,今年还会出版3本随笔集。
北青艺评:写书这点钱,能养活自己吗?
王斌:写作和钱没关系,它的过程让我特别快乐。我是写作不考虑发表的作者了,所以才能写出《游吟诗人咖啡馆》这样的好书。
北青艺评:作为读者,我的看法也许让您不快,您不觉得这部小说的故事量太少吗?
王斌:人类历史上所有好小说的共同特点,就是纯粹。19世纪后,严肃小说已经不再追求什么故事量了,因为小说已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再取悦大众,而是更多转向自我表述,努力呈现个人化思考。
作为编剧,我当然知道怎么讨好观众,设置一个圈套,一环套一环,然后一个反转,接着另一个反转,这就是所谓的故事性。可这种东西只能提供生理性快感,没有思想,也没有精神,无法走入观众内心,不能帮助他们通过观看,逐渐认识自我,甚至不能提供理性快感。
故事量少,因为我刻意与普通读者拉开距离,他们看后会感到茫然,不知道我要说什么,只有读了《游吟诗人咖啡馆》之后,能陷入更深思考的读者,才真正读懂了它。作为写作者,我在内心中也设定了读者的标准,那就是有一定思考能力、有一定知识储备的年轻人。
最好的小说一定是诗化的
北青艺评:在读这本书前,我原本期待它会延续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风格,多一些文本实验,没想到又回到传统的写实主义,您不觉得遗憾吗?
王斌:上世纪80年代时,许多作家对传统写实主义非常不屑,只读先锋小说,越离经叛道,得到的掌声就越多,其实那时的很多先锋作品是伪现代,是借前卫的名头浑水摸鱼。这些作品并没在精神追问上离经叛道,只是在形式上标新立异,其真正追求的是时尚。
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精神故乡是古希腊戏剧,经过这些年折腾,我们该回家了,那就是古希腊戏剧所提倡的,人物,人物,还是人物,把人性作为核心主题。在文本探索之后,我发现,如今很多作家根本不会写人。
古典文学的基本话语是:世界背后是美好的,值得我们去追寻。现代主义的基本话语是:这世界怎么了。我的看法是,绝大多数现代主义创作真正完成经典化的,只有福克纳、米兰·昆德拉等少数作家。而国内的现代主义往往沉浸于游戏感,成了“无聊狗血+口号式台词”,完全没有现代主义写作的精神,没有那种骨子里的反叛。
北青艺评:《游吟诗人咖啡馆》采取了诗化小说的写法,会不会有的读者觉得太老土?
王斌:最好的小说一定是诗化的,因为小说本身就有诗性,几乎所有经典之作都如此。我并没刻意诗化,而是诗意植根在我的心里,转化成文字而已。诗化是追求不来的,只能自然天成。
小说只能展现作家自己的人生
北青艺评:写实主义有一套严格的创作方法论,《游吟诗人咖啡馆》的构思时间多长,您是否曾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王斌:我已经写了7部小说了,都是先有一个大感觉,然后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写得多了,作家自然会变得成熟,一下笔,人物就是活的,不用刻意地去体验生活。其实,每部小说展现的只能是作家自己的人生。
北青艺评:可《游吟诗人咖啡馆》的主角都是90后,比您小很多。
王斌:确实,90后和老一代区别很大,但我依然可以理解他们,我写的就是我。
比如在主角萧朗身上,就有浓重的我的影子,他是理想主义者,虽屡遭现实戏弄,依然能以幽默的方式来回应,他不屑于做不光明正大的事,他的所有行为都可以理解。
至于女主角远乔,则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人,不再那么相信爱,更多靠直觉和感觉,观念相对开放,但在感觉上绝不妥协。再如娇娇,依然相信爱情,但一次偶然,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情爱观,她是已经接受了传统爱情,又主动跑了出来。
不论是远乔,还是娇娇,都有一种冷静,能置身于生活之外去看,她们是我虚构出来的,但许多90后的读者看后,认为我写的就是她。
北青艺评:您不觉得萧朗有点装么?
王斌:我知道你的想法,人们都不再相信崇高理想,任何美好品质,如今都可以被解释成装。我不关心政治,可一次进朋友圈,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川粉,其中很多人还是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因为他们喜欢“不装”,让我震惊。
越是这样的时代,我就越觉得有塑造萧朗的必要。时代拒绝了他,他也在拒绝时代,他走在自我孤独的路上,从不乞求别人。我觉得,萧朗是一只现代的、会思考的虱子,不断行走,走在他思想的轨迹上。在今天中国,一定还有许多像萧朗这样的人,而萧朗将打动他们的心弦。
我倒觉得,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萧朗装。
上世纪末,王朔小说风靡一时,其意义不在文学上,从文本看,他的作品很粗糙,他的意义在社会学上,是对当时一些虚伪现象的反抗。在造句中,王朔故意把意识形态语言套入具体生活场景中,引人发笑。可问题是,在消解过度意识形态话语同时,王朔小说也消解了崇高。负面影响是,很多人把一切文化都视为荒诞,这种意识与国际上的反精英主义形成合唱,他们觉得流里流气就是实诚。体现在写作上,他们特别喜欢意识流,只能记录人类浅层的心理流动,永远达不到真正的思考深度。甚至许多获奖作家都如此,一是不会写故事,二是写到三分之一,就成了强弩之末,剩下的只能挤牙膏,成了毫无生活质感、不生动的“获奖文学”。
纳博科夫只是二三流作家
北青艺评: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上世纪俄罗斯什么都不是世界第一,唯有小说是世界第一,当俄罗斯小说渲染崇高时,可能也预约了俄罗斯后来的苦难。崇高毕竟是建构出来的,是不是也应对它有所警惕?
王斌:许多翻译作品的质量差,所以我很少看,您说的这些我没读到过,如果真是如此,那就印证了我对纳博科夫的评价是对的。我不喜欢《洛丽塔》,也不喜欢纳博科夫的其他作品,我认为他是二三流作家,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俄罗斯作家的那种沉重感。
我不同意他所暗示的,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思想导致俄国苦难命运,不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列夫·托尔斯泰,都曾遭到沙皇迫害,而沙皇迫害他们的理由,恰恰因为他们作品中的崇高感。崇高是超民族、超体制的,也是反抗沙皇暴政的力量。而沙皇们并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如果不知道超验是什么,就不要轻易去否定,而是要给信仰留出一点空间。
人是被语言塑造的,我们说出的每个字,都带有背后的语义,只要我们使用语言,就要接受它的塑造。
北青艺评:纳博科夫一生在用小说抵抗这种宏大逻辑,但他的作品还是很有趣的,不是吗?
王斌:后现代艺术的荒谬,就在于这种有趣。音乐没有主题,叫无调性,把小便池放到美术馆,叫装置艺术。杜尚的创作有观念价值,但没有艺术价值。真正成功的后现代艺术家究竟有几个?有多少创作,能和永恒的古典艺术比?大多数后现代作者什么也不是,因为他们不认真、不阅读,是所谓的空心人。
进入写作,就必须塑造人物,没有这个能力与力量,刻意碎片化,通过拼贴、平面化等,消解深刻。这种小说还需要作家来写吗?没上过学的小朋友也会写,这样创作实在太容易了。我是没兴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