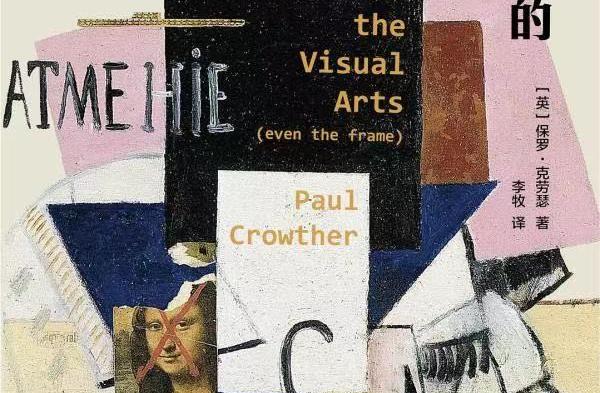“老实人”布鲁克纳是怎么写出那些鸿篇巨制交响曲的?
指挥家吕嘉是一位资深的“布鲁克纳迷”,他曾用“灵魂归宿”形容布鲁克纳,“你听了他的音乐,就像灵魂得到了净化一样,真的非常了不起。”
4月11日,吕嘉将率亲兵——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到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适逢布鲁克纳逝世125周年,布鲁克纳时长一小时的《第六交响曲》赫然在列。这也乐团在音乐总监吕嘉带领下首度来沪演出。
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于2010年,乐手们平均年龄三十多岁,朝气蓬勃,“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声音就是一个年轻的德国乐团的声音。”而之所以带来布鲁克纳《第六交响曲》,吕嘉说,这是布鲁克纳最复杂的一首交响曲,也是代表他最高水准的作品之一。
布鲁克纳常常叫人望而生畏。他是19世纪后半叶最有个性的作曲家之一,几乎每一部交响曲都是鸿篇巨制,不仅国内乐团很少演,国外名团来上海演出时,节目单上也鲜见布鲁克纳的名字。欣赏布鲁克纳需要慧眼,读懂布鲁克纳需要阅历。
在国家大剧院,吕嘉曾和乐评人王纪宴对谈布鲁克纳,通过对谈你会发现,隐藏在鸿篇巨制之后的布鲁克纳,原来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淳朴的农民,而正因为性格里的淳朴、执着、简单、谦卑,让他成为大师,成就了他音乐中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也是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2021中国巡演”里的重要一站。4月10日至17日,在吕嘉执棒下,乐团从北京一路南下,将陆续到访南京、上海、武汉、长沙、深圳、广州。小提琴家吕思清、女高音宋元明、男高音王冲亦将加盟献演。

【对谈】
王纪宴:布鲁克纳是一个非常难聊的作曲家,不管是对于指挥家,还是乐团,甚至是乐曲解说的撰写人,都不敢轻易着手。一般说到贝多芬、莫扎特,相对比较容易接受和接触,但好多人一听布鲁克纳,普遍觉得他太难接近了,中国的乐团演出布鲁克纳也特别少,您能跟我们探讨下原因吗?
吕嘉:我想有好几个原因,一是从乐队的编制上来看,莫扎特是古典音乐的编制,贝多芬最大也是60、70人,布鲁克纳有时候编制很大,有时候要加瓦格纳号。
另外从传承和风格来说,布鲁克纳和贝多芬他们不一样。虽然他们都是德奥的经典之经典,但从个人经历上,他几乎没有什么逸闻轶事。莫扎特、贝多芬有很多故事,因为他们之间有法国大革命,他们都参与其中,他们的人生经历、对人的了解,都与法国大革命有关。布鲁克纳不一样,他是一个淳朴的奥地利农民,正是因为淳朴、执着、简单,成就了他,成为古典音乐中对我而言最高的一座丰碑。
王纪宴:说到农民,也是说到了布鲁克纳最本质的一面,他临死还在家乡教堂弹奏管风琴。有时候他的作品好不容易上演,他出于感激,彩排时碰上指挥说乐谱问题也不会计较。
像贝多芬、莫扎特,我们在听音乐会之前,经常会被音乐之外的东西吸引,这些音乐外的情节蛊惑,布鲁克纳都没有。布鲁克纳一辈子都没结婚,也没什么爱情轶事,那么聆听他、接近他,要走一种直接奔着音乐去的模式,其实是很困难的。
吕嘉:有些人很场面,能说会道,但布鲁克纳这个人,他很真心。“诚惶诚恐”可以很贴切地形容他。他的心肯定是很真诚的,不会做虚假的事。布鲁克纳有个很伟大的地方,对任何人、任何艺术,对自己尊重的东西有一种敬畏之心,比如对瓦格纳,崇拜到就像是他的一个小仆人。他从来没有自大自傲的心,但其实他的心很伟大。他都不知道他的伟大,这就是农民最朴实最好的地方,他用简单概括所有的复杂。
王纪宴:吕嘉指挥所提到的虔诚感、敬畏感,或许是可以慢慢走入布鲁克纳通透世界的切入点。他的作品有宗教意识,这跟他常年在教堂弹管风琴的经历有关。您觉得有没有宗教背景会影响我们欣赏布鲁克纳吗?
吕嘉:会也不会,宗教在西方音乐史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欧洲真正的文化在宗教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来中国,没有什么他不懂的,天文、地理、文学、音乐。利玛窦还给皇帝写过四重奏,所以欧洲的宗教在一定时期本身就是文化的象征。
音乐也是一样,所以慢慢从宗教文化做到世俗文化,比如神剧、弥撒、安魂曲,渐渐个性化,再到法国革命时期的平民化,再到莫扎特时的世俗化。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需要对自己的社会阶级重新判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
贝多芬将自己的精神做到极致。布鲁克纳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不像李斯特沉迷于宗教,最后把自己变成了上帝,成了神父。布鲁克纳一直很谦卑,因为简单与谦卑,他变得很强大,所以到最后,他音乐中的力量是任何人都比不上的。
布鲁克纳是对位法作曲家,所有和声的转换都是根据低音来的。布鲁克纳的音乐是利用和声来做力量与音色的变化,没有一点多余的感觉。他的重复是取之不尽,不断更新的东西。虽然布鲁克纳有自己的写作技巧,但你总是能透过音乐,听到他的真心、他的简单。布鲁克纳永远是“空”的,所以才能不断接受更多美好的东西。也正是因为他的简单与谦卑,他才能成为大师。
王纪宴:您说布鲁克纳的音乐是个通透的世界,太能说明布鲁克纳的美和价值了。
吕嘉: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入境,有就是没有。虽然有点玄乎,但是有一定道理。如果脑子中存在太多自己的东西,就感受不到周围美的人、事、物,因为你太主观了。
 布鲁克纳
布鲁克纳
王纪宴:谈到民间色彩,您觉得布鲁克纳的作品对奥地利民间乐曲的运用,与马勒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吕嘉:一个人的个性如果非常强烈,他不可能有很多朋友。音乐也是一样,如果把一个民间小调原封不动地运用在交响曲里、歌剧里,几小节可以,但如果一下演奏半个小时,那就很不一样。比如一个朋友有个性、有脾气,5分钟是个性,一天都这样就会烦了。音乐中充满个性是好的,但同时音乐也会被个性局限。
马勒的音乐很伟大,但他的伟大之处来源于他生活中的些许不幸,犹太人,天主教,家庭不幸福,孩子去世得早,夫妻关系又不好,诸如此类。马勒很倔强,个性十足,长此以往,他去维也纳、纽约久了,别人会赶他走。马勒作品中有他的酸甜苦辣,然而每个人脑子里想的东西,并不是别人能完全接受的。他把自己最痛苦、宝贵、带有暴力倾向的东西都写进去了,听久了会觉得太个性了。
马勒的音乐与布鲁克纳有很大区别,也有相同之处:宗教和自然。
马勒《第三交响曲》就是纯自然,马勒想要得到他在生活中、做人中得不到的解脱。他只有在天堂中得到解脱,而且他的天堂里都是小孩。我们在马勒作品中能听到女高音唱出的小孩的声音,马勒不要上帝,他要天堂,孩童一样无忧无虑、天真无邪,这是他的精神上的天堂,马勒只能寄托于这。
布鲁克纳也在他的音乐中找到了天国,不同的是,他在生活中本身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简单质朴的孩童。二人在音乐中流露出来的对于宗教和大自然的感受是相同的。虽然技法不一样,马勒的作品中囊括了更多很个性的写作手法。但是追根溯源,二者在艺术追求上还是有些许共通的。
王纪宴:布鲁克纳写交响曲时在维也纳已经生活了13年,他是有名的管风琴家,但作为作曲家始终不能得到充分的承认。《第六交响曲》写过后,只有雨果、伍尔夫、马勒特别崇拜他。去世两年后,他的乐章能够正式演出时,指挥正是马勒。大家对《第六交响曲》了解较少,您能说说对它的印象以及它的特殊地位吗?
吕嘉:《第六交响曲》是承前启后的作品,是布鲁克纳中晚期的作品。布鲁克纳逆来顺受,所以他的幸福感很高,他看待世界,自己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只要有些细小的回报就很满足了,这种满足感在他的交响乐中也是有迹可循的。
布鲁克纳的前几部交响乐作品几乎没有得到认同。他的《第三交响曲》是献给瓦格纳的,虽然大获成功也未能久存于世。但是瓦格纳对于布鲁克纳的才华确实赞赏有加,曾评价说“贝多芬之后,唯一能够继承贝多芬衣钵的人只有布鲁克纳,因为贝多芬之后所有人都是诚惶诚恐,不敢写交响曲”。这个评价极其之高。
从《第四交响曲》开始,虽然还有以前的痕迹,但他的个人风格也愈加凸显。布鲁克纳最好的作品是《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但是如果没有《第六交响曲》,也就没有这两部完美呈现布鲁克纳成熟风格的巅峰之作。
《第六交响曲》是最短的一部作品,全曲约五十六分钟,其他的交响曲每首都有一个多小时。虽然《第六交响曲》不是很长,但每一个乐章都非常完美。从写作技法来说,人们都觉得布鲁克纳最出彩的都是某些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其实他的第二乐章都写得很好,第三乐章略有自然的烙印,其中有他所惯用的铜管乐与弦乐对比的写作手法。
另外比较特殊的一点是,因为布鲁克纳是个很老实的人,所以他可以接受别人修改他的作品。这些改动有些精炼了作品,有些却改变了他创作的精华。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大多都是根据指挥的好恶而修改的版本。总体来说,《第六交响曲》每个部分都很精彩,又不失精炼,编制也不大。
 吕嘉
吕嘉
王纪宴:很多听众关注更多的是好听指数,布鲁克纳的交响曲与其他作品的好听指数会不会不一样?
吕嘉:我们说到越有个性,可能合得来的人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的音乐太没有个性的话,就变成了“老好人”,这样也不行。老好人加之深度和厚度,那就是对的。
音乐也是这样,拥有了深度和厚度,就有了不一样的世界。比如他的《第九交响曲》最后乐章,很有激情,又很睿智,平静地看待自然、人生。有些时候你会觉得音乐在宇宙里超脱了,这种超脱是有功夫的,这就是他的伟大,他的简单、丰富。
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农民,他没有见过世俗的东西,花言巧语,名牌,维也纳社会流行的尔虞我诈。他根本不懂,也不去效仿,但就因为这样,别人的弯路他没走过。他集中在一起,爆发出伟大的音乐。回归到自然的空灵,也就造就出纯净深奥的好听的音乐。
王纪宴:像布鲁克纳这样的奥地利农民大师,可能历史上就这一个。这可能跟我们中国人坚持的观点背道而驰,我们总认为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但我们看布鲁克纳就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老头的模样。
他跟瓦格纳的关系也让他自己受到连累。有一本书叫《论音乐的美》,作者汉斯立克因为讨厌瓦格纳,始终攻击布鲁克纳。布鲁克纳因为没有反击能力,以至于被评论家做手脚,很多作品演奏不了。布鲁克纳成了名家之后,皇帝接见他,他就提了一个要求,请汉斯立克别再写文章骂他了。
吕嘉:当时维也纳汉斯立克一派可谓是穷追猛打。瓦格纳已是一方霸主了,可以完全不在意这些评论家。布鲁克纳从排位来说,充其量也就是瓦格纳身边的一个小马仔,好欺负。汉斯立克推崇勃拉姆斯,当时还处心积虑地使得勃拉姆斯与瓦格纳相互为敌。当然,最终两位大师也和好了,因为他们都了解到对方的伟大之处。
布鲁克纳去世时,维也纳几乎是国葬,当时说勃拉姆斯躲在房檐下落泪,虽然这可能是演绎,但当这样一个对手离开的时候,勃拉姆斯的心里是空空的,因为最伟大的敌人也是最亲近的朋友。
王纪宴:所以那个时代很有意思,风格很不一样的伟大的作曲们家,像是瓦格纳、勃拉姆斯以及布鲁克纳,他们都生活在同一时代。
吕嘉:我觉得那时候是欧洲的第二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以但丁、达芬奇、薄伽丘等伟大作家、画家为代表的。400年之后,意大利、德国、沙皇都开始成气候,奥匈帝国趋向没落了,历史变更肯定能碰触出很多火花。第二次文艺复兴仿佛到来了,涌现了音乐界的拉威尔、施特劳斯,绘画界的毕加索、伯克利,文学界的卡夫卡、茨威格等等名家。你可以想象,文坛、艺术上人才辈出,不断地影响着21世纪。那之后就是一战二战,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发展,后来就是个人主义居多,文化似乎就断档了。
王纪宴: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很怀念那段时期,整个19世纪下半叶很繁荣。当时,布鲁克纳还是执着于自己的音乐世界,谦卑地谱写着自己的音乐,这份执着对于他的音乐风格的发展有何种影响呢?
吕嘉:布鲁克纳不受维也纳人待见,最后几年算是功成名就了,最后连汉斯立克都挑不出毛病,只能说他写得太长了。我很佩服他的执着,因为艺术家需要执着,其实一开始不需要聪明,反而容易被聪明误。你达到一定高度,获得了一定积累,不论是学术、生活,还是知识、思想,到了集大成者之后,你的聪明会帮你无数的忙。但在那之前,聪明会害了你,因为聪明的人随时在变通,随时在找机会,就不会坚持。坚持真的太重要了,比如孟京辉,坚持到现在,就是成功。
有时候,你一定要付出到仿佛上帝觉得足够了。虽然我觉得艺术永远没有足够的时候。我现在看我去年指挥的东西都会觉得很不满意,因为艺术上是需要永远保持进步的。艺术追求永远没有尽头,只有积累到一定时候才能获得自我提高,从而给观众和乐队队员带来一种美好的享受。
王纪宴:我非常同意您刚才这段话。您刚说的聪明,我老是联想到老鼠的聪明,反应特别灵敏,调整太快,丧失了方向感,反而最后比它笨的人成了大器。
吕嘉:因为你积累到一定程度,你上的台阶不一样,眼光、境界不一样。如果只是小聪明,就像老鼠一样永远在阴沟里看月亮。
那时候维也纳人非常势力,穿得不好,长得不好,就会给你白眼。布鲁克纳就是他们不屑一顾的对象之一,但是最后他成了大器,很大一部分需要归功于他特有的简单、质朴和宽广的心胸。因为他不计较,对很多事无所谓。同样的情况,如果是莫扎特、贝多芬,他们会暴躁,如果是李斯特,他一向视自己为神,根本不会予以理睬。然而布鲁克纳没有什么,他会觉得可能是自己做得不好,再去改改。
生活中很多事很难估计,我觉得最要紧的是做最真实的自己,认定了一条路,就走下去。当然在现代社会也需要一定技巧、方式,但最重要的就是坚信自己,坚持下去,早晚会成功,我想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国大管弦乐团
国大管弦乐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