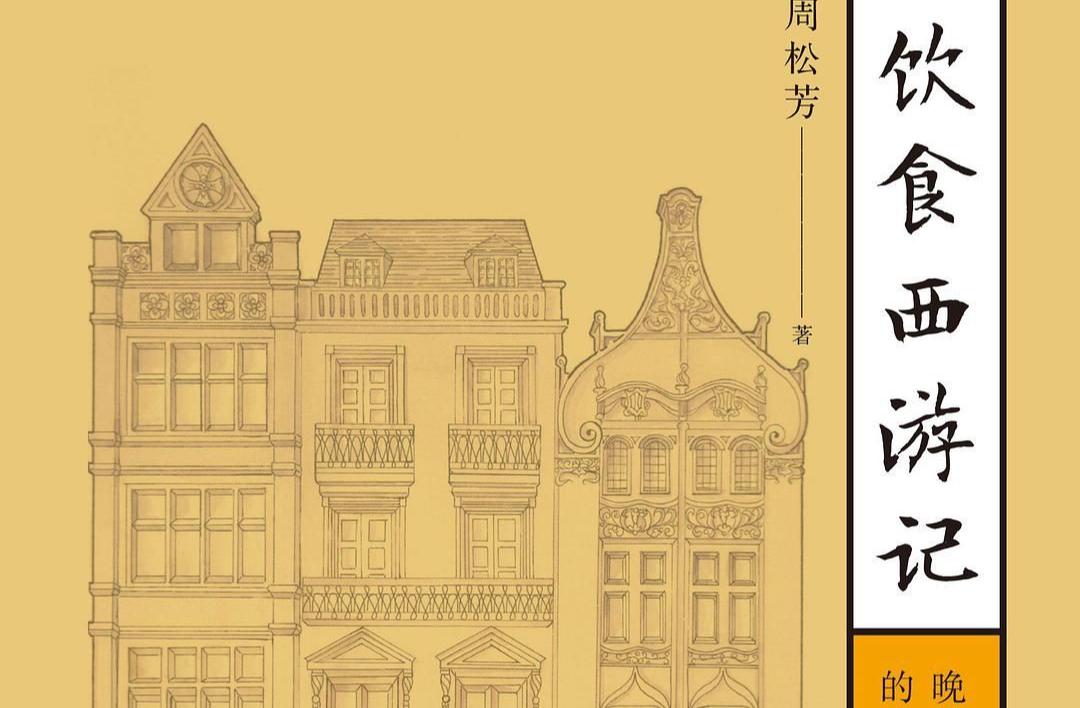逐梦太空 最亮的中国色彩是“青春”
嫦娥神舟团队年均33岁,北斗团队年均35岁

2020年7月23日12时41分,中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火箭飞行约2167秒后,成功将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入预定轨道,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迈出了中国行星探测第一步。 人民视觉供图

2020年7月21日下午,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外的海滩上,一位男子身穿 “太空服”,变身“火星宇航员”,在即将发射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的火箭发射塔架前往来穿梭。 人民视觉供图
浩瀚太空再次迎来中国人。6月17日,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名航天员乘坐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在距离地球几百公里的高空,他们要组装建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太空之家”——中国天宫空间站。
从古时万户飞天,到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飞向太空,再到如今的筑梦天宫,中国人探索宇宙的脚步从未停歇。这背后,是一代代拥抱航天梦想的中国人,悄然将青春容颜变成了皑皑白发。
1950年,身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学院最年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为航天报国作出回国的决定,那一年他39岁;2003年,杨利伟乘坐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进入太空,那一年他38岁;中国首批女航天员刘洋、王亚平飞天时,均为33岁;前不久刚刚宣布圆满成功的中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80后、90后青年更是其中的主力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航天报国的嫦娥团队、神舟团队平均年龄是33岁,北斗团队平均年龄是35岁。
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中,青春成为中国航天最亮丽的色彩之一。如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前局长所感慨的那样,“中国航天最厉害的,不是它取得的像载人航天工程这样的巨大成就,而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科学家和工程师”。
——————————
创业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一首《东方红》乐曲响彻寰宇,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的序幕。
长征一号点火发射的那天夜里,陈克明是最后一批从发射塔架上撤离的人,这位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参与长征一号第三级固体火箭发动机研制的功勋设计师,要对固体发动机进行最后的检查。那一年,他34岁。
要发射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离不开运载火箭提供的强劲动力。1965年,一群年轻人毅然来到内蒙古的戈壁荒滩上,开始了我国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拓荒。这其中,就包括陈克明。
研制初期技术不成熟,常会遇到发动机故障甚至剧烈爆炸的危险情况。陈克明记得,当时一共进行了19次试车,其中前面13次均以失败告终。
“回顾过去,航天事业确实是创业维艰,特别是固体动力事业,白手起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粗到精,直到跻身于国际前列,走过了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陈克明说。
他参加了这一型号的研究、设计、试制、试验直至发射飞行试验的全过程,“整个过程下来我无比自豪,这让我同祖国的航天事业结下不解之缘,毕生难忘。”陈克明说。
他至今记得,197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部分研制人员受到中央领导接见的场景: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戚发轫,以及他本人在内的17位东方红一号任务研制人员,在那晚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我们一上来就被直接领到城楼西侧,虽然给每人安排了座椅,但大家没有一个落座的,都被广场上那红火热闹的场面所吸引,灯火璀璨,人山人海,喜庆的锣鼓声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陈克明说。
同样是那一晚,作为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子弟的杨世杰,从父母的话语中得知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消息:那天中午,一向“抠门儿”的父亲,从扁扁的钱夹子中捏出1元钱给他:“买三挂小鞭炮,你们兄弟仨一人一挂,晚上咱们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飞过来时放。”
大约晚上8点,天上的星星和月亮被云团遮挡得严严实实。杨世杰记得,大家小声嘀咕着:乌云能挡住卫星吗?卫星飞过来时能看到吗?就在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担忧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登高远望”的提议,七八个人便上了杨世杰家所在的家属区北边的土山坡上。
不知又过了多久,从山坡下传来一声又一声呼唤他们回家的声音。杨世杰记得,大家一边恋恋不舍地往回走一边说,天上的卫星一定会看到他们的,因为他们站在高高的山坡上,因为他们身旁有一堆熊熊燃烧的火焰。后来,这些年轻人中,有不少接过父母的衣钵,成为新一代的航天人。
扎根
今年,有着41年党龄的老党员、77岁的中国航天科工六院46所研制专家杨佩娟在整理过去留下来的东西。一封钱学森给她写的信又一次拿在手上:“杨佩娟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了……只要坚持在工作中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快胜任目前的工作,并且作出自己的贡献。”
杨佩娟第一次拿到这封信是在1966年,那一年,她22岁,刚工作没多久的她给钱老写信诉说自己的困惑:自己大学所学专业与工作内容对不上,怎么办?
1965年,我国首个固体火箭发动机研究院——七机部第四研究院(现中国航天科工六院前身)搬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建立起了新的研发生产基地。也是这一年,杨佩娟大学毕业,离开上海来到七机部第四研究院。
毕业后分配工作单位时,杨佩娟有不少选择,但她决定去内蒙古:“哪里最艰苦,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去哪里。”从此,她扎根在塞北,再也没有离开。
“前几天沙尘暴,好多人都第一次见那种场面,但我都习惯了。”杨佩娟说。当年她刚到内蒙古时,也是看着满天的黄沙瞪大了眼睛,“从上海到内蒙古,像是两个世界”。
在上海,杨佩娟家住在静安区南京西路的张园,现在“流金淌银”的南京西路当时也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之一,张园弄堂的石库门上雕着西式雕花,她上学路上会路过戏院、电影院、舞厅……来到内蒙古后,大家总叫她“上海姑娘”。走在泥地里,杨佩娟动不动就“啪”地摔一跤——来内蒙古前,她甚至没怎么走过土路。
但生活上有多苦,杨佩娟都不在乎。她来到内蒙古,想用自己所学为国家作贡献,却发现使不上劲——自己的专业跟实际工作需要不对口,这让她十分着急。迷茫中,她便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苦恼,没想到竟然收到了回信。
钱学森在信里说:“我们在大学里所学的那一点东西,比起事业的需要来,是很不足道的,大量的知识点只有在实际工作中才能学到……”
上大学时,杨佩娟非常敬佩学校里的老师:“他们怎么能做得那么好,给国家给人民作那么大的贡献,我能像他们一样吗?”现在,这个问题有了答案。扎根塞北草原50多年,杨佩娟的青春年华都写在了这里,她本人也成为我国航天固体动力事业分析测试领域专家。
“人活在世上得有一定的价值,能力是有大小的,我想,我把我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了。”杨佩娟说。
传承
如果说老一辈亲手编织了中国航天的“摇篮”,作为“航二代”的王文斌,则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航天二次创业的辉煌。
上世纪60年代初,航天事业急需大量技能人才的加入,凭着严格“政审”关的章章红印和一手过硬的钳工技术,特别是党员这一“名片”,王文斌的父亲调入北京航天科技一院,成为航天事业的一员。
“常听老人说,这一辈子最不悔的追求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做的最正确的事就是投身航天事业。这两件事是老人这一辈子值得荣耀和留下满满回忆的事。”王文斌说。
当一纸调令递到眼前时,老人二话不说,全家五口搬迁北上,于上世纪70年代初来到内蒙古,加入塞外航天建设大军队伍。从在北京住三层有暖气的楼房,到住在靠自己生火取暖的砖土混合平房,从能够吃到限供的大米白面到天天吃限供的玉米面及杂粮。
在王文斌的印象中,土豆、白菜、胡萝卜是四季中最难忘的菜品,父母亲在空余时间还开垦了一块自留地,种些应季的蔬菜,才有了些口味的变化。王文斌在北京出生,在南苑东高地“四小”上学,来到内蒙古,由于子弟学校课程不全,有时课本都不能及时发放,让他的小学时光“放飞”了好几年。
提到这些事,王文斌曾经问过父母,从首都北京举迁到塞外呼和浩特,后悔吗?老父亲说道:“那时候不知道啥叫后悔,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也是事业的需要。”说这些话时,父亲表情严肃、态度坚决,王文斌就是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成长起来。
后来,军校毕业的王文斌,转业回到内蒙古基地,踏上了“航二代”的航天建设之路。如今的他,也即将步入花甲之年,很快就要离开这份从事了30年的航天事业,老父亲还健在,他也可以亲口告诉父亲,自己无愧“航二代”的身份。
这样的传承,既在一个家庭上演,也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乃至整个航天领域上演。有时,在领取一些重要奖项时,中国航天科工的科技领军代表都不露面。许多的“张总师”“王总师”“刘总师”在公众面前仍然默默无名。或许几十年之后,他们才能够为世人所知,就像今天人们知晓钱三强、邓稼先、于敏、程开甲等老一辈军工人几十年前的事迹。
从半世纪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到神舟五号飞船实现中国人飞天梦,再到嫦娥一号开启中国探月之旅,不同时代的热血青年投身航天、挑起大梁,铿锵有力地诉说着“为国铸剑”的壮志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