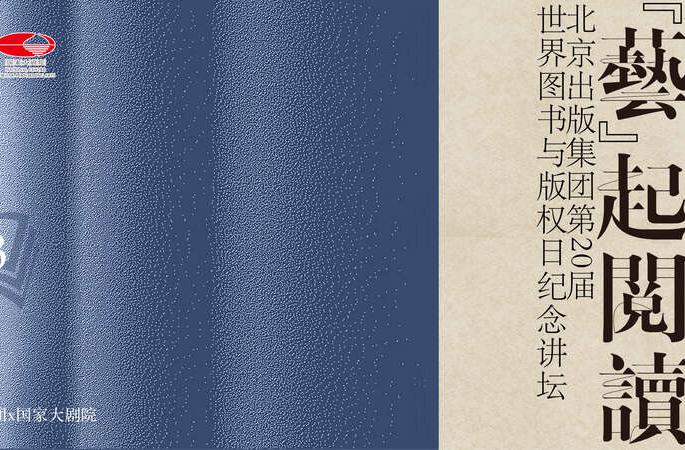上海骑手的15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
已经到缺调味品的时候了。
4月14日,上海市长宁区,饿了么骑手黄明接到一位居民帮买盐的电话,对方说“没有盐,抢的菜也没法吃”。黄明骑着电动车跑了半个多小时,问了5家店才找到盐。
他买了最后10包,1包给那位居民,剩下的留着备送。骑手群里已经有人在问“哪里有盐”。
另一位同时跑蜂鸟和顺丰等4家平台的骑手岳冬川,也接到客户电话,请他帮邻居买盐。最终,他没买到盐——买了两罐豆瓣酱。对方没提加配送费,他也没说,“塞袋里顺手送了。”
“大上海可能不缺物资,但是感觉非常不均衡。”岳冬川说。
接受采访的骑手们否认最近传说的“日入过万”,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除非当天接的全是路线单一、奖励金额高的企业单,“要不那心得黑到啥程度?”

4月13日,上海街头的一名骑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他们决定去跑单
4月10日,黄明接到公司催他出来跑单的电话时,已经吃了一周的老干妈辣酱拌饭。
他所住的小区因有密切接触者,从3月26日开始封控管理。当时的消息说“封4天”。黄明和3个安徽老乡兼室友一起买了5公斤大米、少量青菜,早上睡醒吃一顿、下午饿了再吃一顿,想着“4天怎么熬都能熬过去”。
没想到,4月1日小区没解封。当时社会和企业不断呼吁“释放运力”,两个室友决定外出跑单,代价是出去就不能再返回。
黄明被同在上海打工的妻子劝住。妻子说,病毒对人肯定有害,不管大小,如果感染隔离,“活儿也白干,别冒险了”。
他和另一个舍友花280元买了25公斤大米,并收到社区发的1包泡菜、3颗洋葱和几个土豆。
4月1日这天,住在集体宿舍的美团骑手张年也决定和7个舍友外出跑单。除了响应“释放运力”的号召,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吃腻了方便面。集体宿舍没有厨房,只能用唯一的电热水壶烧水泡面,嗡嗡地几乎从早烧到晚。
张年说,离家打工都是为了挣钱,在宿舍待着肯定什么都挣不到,不如出去碰碰运气,而且他具备在疫情中工作的经验。
张年26岁,到上海打工前,在武汉送外卖。2020年初,武汉疫情暴发时,他被迫退掉腊月二十九回河北老家的车票,在租住地——一座有100多栋居民楼的社区,当志愿者。
“那时想法跟现在差不多,都是为了吃饭、生存,出来当志愿者有饭吃。”张年表示,出租屋里什么也没准备,5个年轻舍友全都到小区当志愿者,大家有力气、熟悉路线,帮助社区卸菜、送菜、消毒。
当时,他们真正地在跑“最后一公里”。政府分发的物资拉到小区门口,他们卸车后往各个楼栋送。
武汉早期疫情猛烈,他们光着身子穿防护服,戴着大号尿不湿,小便、大便都在里面解决,直到晚上睡觉才能脱掉冲洗,住在临时搭的棚子里,不能回楼里住,“武汉那时候真苦,但是大家目标很纯粹,就是那几项任务,效率高。”
20多天后,武汉疫情稍缓,越来越多的社区年轻人出来当志愿者。张年等6人抽出身干原来的活儿。他们所在的外卖站点,经当地指挥部协调,接受了为居民配送药品的任务。
“每天有一个人专门钉在那里,往我们身上调单。”张年回忆,药店开门后,他们只负责取药、送药、送酒精,前期求药信息、诊断、配药、找药已有人完成。封的时间长了,许多居民特别是老人缺药。
“送药是有偿的,跑一单能拿一单的配送费。”张年表示。
张年觉得,武汉一开始措手不及,比如他们所在的小区居民储备普遍不足,大概前十天特别难,但大批物资到后,能做到快速分发,“不愁吃、不愁喝”。
在武汉封了76天后,张年重回街头送外卖,由于平台配送费一降再降,到最后“一天也跑不出什么钱”,转到上海打工。上海一单大约能高2元,“一天跑50单就多挣100块钱。”
这样在上海一干就是两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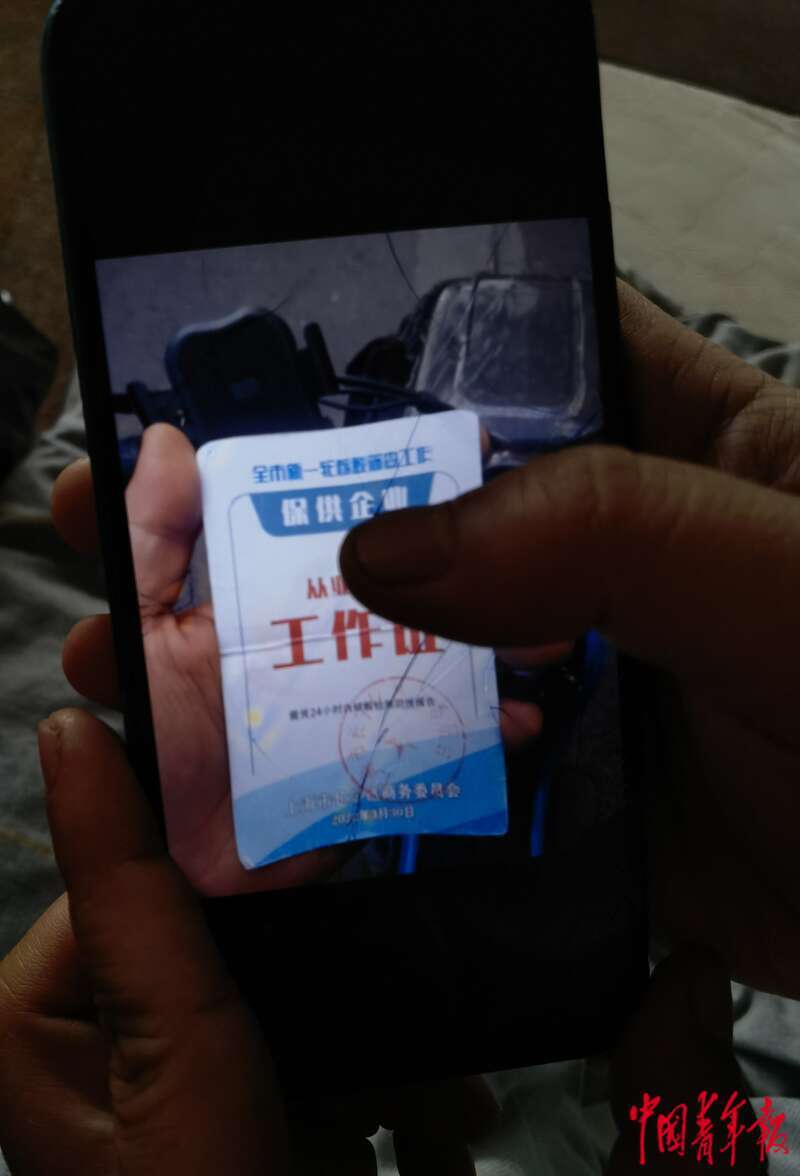
一名骑手手机里的“保供企业工作证”。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4月3日起,张年的小区通行证不管用了。一些平台公司称协调定点酒店,实际上并没有向他们开放。酒店的理由是“价格没谈妥”“属地有规定不接待流动人员”或者“被征用”。他让没出来的朋友把被褥从窗户扔出来,住到一座高架桥下。
4月10日,黄明和室友的泡菜、洋葱、土豆早已吃完,老干妈玻璃瓶见底,他把瓶子塞进垃圾袋系紧——他们再也不想闻到辣酱的味道。
他们第二次收到社区发的“蔬菜包”:2根胡萝卜、2个土豆、2个西红柿、1块姜、几瓣蒜和1盒罐头。
黄明把这些菜分给邻居,决定出去跑单。
“全变了”
走出小区,黄明才发现外面的物价已十分离谱:10公斤东北大米,160元;5升装的菜籽油,以前130元能买2桶,现在只能买到1桶。一位客户想吃橘子,市场的摊贩不按斤卖,按个卖——每个5元。客户在微信视频那头也惊呆了,表示“吃不起,不吃了”。
仅封控14天,黄明感觉自己像一个初入江湖的新手,以前熟悉的卖家、市场换了一副模样。
他尝试着向商家讨价还价,对方态度强硬,“不买就可以走”,更多的时候压根儿不理他,因为仍然有很多人买。
岳冬川等早出来10天的骑手们已熟悉了这个新江湖。有货和有渠道拿到货的人是“大爷”,跑腿的骑手和下单的居民都处于弱势地位。
接单形式、取货方式和送货路线都在重构。
骑手一般分为专送骑手和众包两类。张年解释,虽然各家平台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简单理解就是专职和兼职的区别。
专职骑手供职于一家平台,工资以月结为主,由系统派单,负责一定范围的商圈,优势在于每一单配送价格较高、稳定。兼职骑手更自由,收入日结,可以接全市、跑全市,配送费不固定,可以同时在多家平台兼职,但是需要抢单。
一名专送骑手打开手机上的骑手系统向记者介绍,地图上的红色圆圈代表他们站点负责的商店,颜色越红、外卖单越多。封控管理以来,许多商店停止营业,或在偷偷营业、不再线上展示,骑手很难在系统上准确看到货源和店铺营业信息。派单量急剧减少,许多专送骑手也转向跑众包,帮买、帮送。
在众包骑手登录系统后的页面,记者看到,“大厅”里展示着一列看不到尾的待派单。张年说,放在疫情前,大家扫一眼就能判断是否抢单,现在,不但要看距离、路线、价钱,最关键的,要看具体买什么。
以往的路不一定通。上海的骑手多集中在静安、黄浦、徐汇、长宁等市中心及附近区域,这些区域遍布知名店铺、商超和商业步行街,正常状态下每天发出大量派往全市的单。现在,商店普遍关门,骑手无法前往浦东,其他地区的路线也需要重新考虑——因为不清楚哪条路已经“断了”。
岳冬川在闵行区遇到许多次临时封路,地图显示可以通行,到了路口才看到有围挡,“手上的单不能放弃,第一次只能绕路,要绕很远,想尽办法都要给人家送过去,但是再看到那些区域的单就不接了。”
4月6日前,他们很少送蔬菜、水果,因为没有货源。有时,货源充足的菜场老板不卖菜给骑手:只接团购单,比如单价188元、288元等高价的蔬菜包,不接受他们在里面选购。
他们尽量避开小店、菜场,挑选货源时优先到连锁便利店、中大型的商店,为顾客购买尽量明码标价的货物。运气好的话,他们可以拿到购物小票,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沟通上,直接无接触配送到小区门口,拍照走人。
“这是早期有货的时候。”岳冬川强调,到后来便利店基本被扫空,只剩水和便当。商超一般对接大客户,骑手取货比较难,并且,他们不确定哪些商超在营业,有的大商场只打开仓储后门。
商店开门具有相当大的随机性,并且开门只是打开一条门缝。他们的经验是,如果你看到门口站着骑手,这家大概率在卖货。
如果没有明码标价,他们会和客户打开视频通话,让客户看到货物、听着报价。对方如果决定买,就会把购物款转给骑手结账,等货送到了再给跑腿费。
骑手会在各自的群里分享一些卖货的商店,在路上看到手里有货的骑手,会询问在哪买到的。
“大家都会讲,没见过垄断的。”岳冬川表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家店明天可能就不再开门,只能再重新寻找,“1个骑手找不到,100个、200个总会找到。”
求购其实在求助
在封控管理前,骑手们不太喜欢接帮买单。
“太费事。”岳冬川解释,平时送单,从A点送到B点很快,疫情前这种帮买单,这里要一个、那里要一个,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一次买齐。
现在则以帮买单、帮送单为主。“实际上这是封在家里的人在求助,他们实在缺少物资或药品,请我们这些还能在外活动的骑手帮忙。”这也是为何现在一些骑手脱离平台交易的原因之一。
有言论指责骑手脱离平台交易挣“黑钱”,呼吁居民保留交易证据,等上海恢复常态后向有关部门投诉。
岳冬川说,脱离平台是有原因的,居民和骑手都有苦衷,“外面的人可能不清楚求助居民的现状。”
封控管理以来,能在街面上活动的群体不多,骑手是其中之一,但是当前出来跑单的骑手数量有限,居民下单多数时候迟迟无人接单,一旦联系上一名骑手,会立即要手机号、加微信,与邻居和朋友拉群,如果再有帮买、帮送的需求,会直接联系骑手帮忙。
受访的几名骑手都已加过上百个微信号。有时忙不过来,骑手们会互相分担求购信息。
“私下单的跑腿费一般每单50元,根据距离、货物的数量和重量,再与客户商量,100元一单的属于高的,但是很少。”岳冬川说,这个价格其实并不高,“你想想,平时的同城急送一单需要多少钱?”
并且,疫情下,还有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时间,找货、排队、绕路的时间。一名骑手接了一个买可乐的单,跑了一下午没找到,他想把100元跑腿费退掉一半,但是对方没收。
私下求助的居民也并不是天天求购,如果能买到,他们基本是一次性让骑手买大量的货物。岳冬川说,接单还是以平台单为主,平台整合了全市的需求,也节省沟通成本。
有些私下求助信息令人揪心,如果能做到,他们不会劝其找别的渠道。比如,婴幼儿的奶粉和尿不湿,骑手们近乎达成默契,看到后一般都会迅速接单。
在徐汇区,岳冬川接到一个女生求帮买药的单。他们轻易不接买药单,因为买药需要排长队,也容易碰壁:药房对处方药有严格要求,有时要报身份证,查购药记录。
这次,岳冬川身后就是一家药店。但对方说,她的药是治抑郁症的,必须到精神卫生中心去买。
到了医院,看到望不到头的购药队伍,他想放弃。那名女士称“情况很急,手里没药了,想跳下去”。最终,他顶着大太阳排了3个多小时的队买到药。那名女士额外给了100元小费。
一名骑手接到“送人”的信息。客户是一个急性肠胃炎的年轻人,疼得满地打滚,“肠子里像刀刮”。打120、110都要排队或需要自己核实医院接诊才可以送。他出100元让骑手带到医院门口。
那个年轻人几乎是爬着从小区出来的。这名骑手用电动车驮着他,骑行十多公里从虹桥带到徐汇,寻找可能接诊的医院。
张年在一个封控小区遇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老人可能不会网购,也好像不清楚外界发生了什么,站在小区门口旁的栅栏里,像在菜市场买菜那样问前来送单的骑手,“您这个怎么卖?”“多少钱一斤?”“有鸡蛋卖吗?”
张年看到时,想掉泪,因为那个老人像自己学不会用智能手机的爷爷。他告诉老人,这都是人家订好的,要从网上下单。他买了一箱鸡蛋送给了老人。
在疫情前,骑手们喜欢送单的地方是医院、学校、楼龄较新的小区和高档小区。
“因为这些地方通常不让骑手进,放在门口就行,省时省力。”张年坦陈,老旧小区、公房物业力量不足,经常会遇到可以让骑手进、但不让电动车进的情况,这些小区的楼层普遍低、没有电梯,楼栋牌号不清楚,骑手很容易迷路。
这些小区在封控后,问题更为突出。张年说,平常不用骑手送到家门口的,除非那个小区疫情非常严重、物业和保安遭受重创,一般仍可承担小区内的配送,何况还有志愿者。
而老旧小区和公房则令人担忧。张年租住的小区由10余栋6层的公房组成,100余户,负责小区的只有几名保洁员和保安。
因为有张年等骑手租户在外跑单,该小区不缺物资。张年拉了微信群,大家定期接龙下单。之前能进小区时,他们直接把物资送到楼门口。自从小区通行证失效,物资如何再送到楼门口成了难题。
有人向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距小区较远,人手也不足,让楼里派代表或推选志愿者,由于该小区本地老人、外地人较多,平时走动少,也没推选出结果。
最终,张年想出个主意:按每趟10元的费用动员小区保安多跑腿。“疫情以来,保安也挺辛苦的,很多来自外地。”张年说,多给他们一些物质激励,比协调楼里的人容易。
骑手的非战斗损失
顺丰骑手“日入过万”的消息一出来,就在骑手圈引起热议。张年说,当时大家认为是假的,即使是最牛的“单王”,这种状态下每天跑五六十单几乎已到极限,只有一种可能:那名骑手接到了企业单,还是相当高的打赏单。
“顺丰同城”的官方回复印证了他们的猜测:那名骑士共完成60笔同城配送订单,系企业用户下单,订单佣金计提总额达10067.75元。其中包括用户打赏约7856元。也就是说,该骑士平均每单不含打赏收入为约36.9元,平均每单获得打赏约131元。
岳冬川4月9日接到过类似的单,从徐汇一家医院拿中药挨家挨户送,一共37单,总收入1300余元,没有打赏。
“这种单很累,要尽量快速送到。”他那天没有吃午饭,从早上九点送到下午三点。
张年的最高收入纪录是一天3000多元,从早8点到晚上10点,跑了40多单,当晚腿伤复发。
张年说,这些天确实是挣到钱了,但高峰期已过,或者说是货源越来越难找。几位骑手向记者展示收入:从最高峰的3000多元,到千元左右,最少的一名骑手一天跑了9单挣到200元。
封控以来,骑手们最担心的是生病、红码和摔车等意外。
从4月2日至9日,张年没有吃过热饭、热菜,因为住在桥下,没有热水,车上放着一摞面包、瓶装水,但是经常吃不下,“面包太干。”张年说,他三天没有大便。很多公厕都封了,这十几天他们没洗过澡,也没洗过头,早上醒了用湿纸巾擦脸。
4月10日,一家连锁便利店开门,卖盒饭,热米饭、热菜。张年扒着门缝买了三份,坐在门口台阶上往嘴里塞,一口气全吃光了。
岳冬川表示,在外跑单,他们要保持24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几乎每天要去医院花40元自费检测,出结果后上传至平台,并在卡口随时接受检查。
4月13日,上海迎来封控以来的第一场降雨。当天下午,上海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张年、黄明和岳冬川等骑手均未外出跑单,他们没有带够衣物,长期睡在水泥地上,担心再淋雨可能会发烧生病,影响跑单。

4月13日,上海降雨降温,一名骑手还在跑单送货。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耿学清/摄
他们只有一项商业保险——每天开工平台扣3元保费,没有其他保障。骑手的口罩普遍也是自费买的蓝色普通口罩,“买不到N95,也贵。”
下雨天路滑摔车更令他们担心。张年说,自己摔伤没事,长期跑单不可避免,主要是担心摔坏货物、车子和手机。尤其是摔坏货物,不仅白干,还要赔偿。
这些天,张年经常看到路边推车走的骑手,不是电量耗尽,就是车子出故障。
骑手的电动车分为换电和充电两种车型。换电需要到车行或自助换电柜。封控以来,许多车行关门。自助换电柜多位于楼宇内部或城中村里。可供换电点减少,骑手估摸着电量接单。
黄明的车是充电式的,他找到一个环卫站,每天塞给管理员一包烟,晚上在那里充一次电。
一些修车行与骑手达成默契,车出故障后,骑手把车放在车行门口,发送信息后离开。车行老板修好后,把车再放到门口,等骑手自行推走。
“现在最大的想法就是就早点儿恢复正常。”岳冬川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黄明、岳冬川、张年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