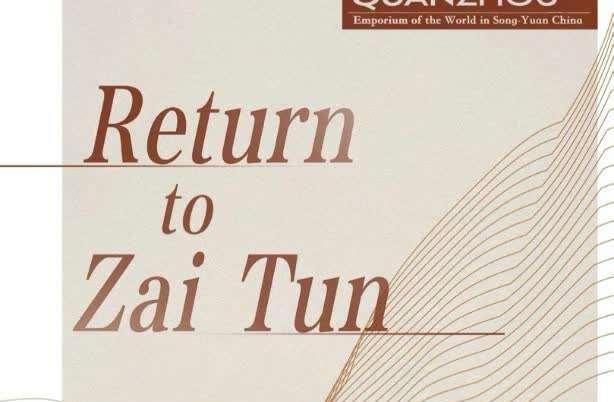朋友在哪里
在北京,见朋友是件困难的事情。
9月的一个周六,我约半年多没见的大学同学吃饭,当天上午8点多,一个朋友说来不了了,领导通知9点半开会。于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吃了一个小时,买了一份糕点后分道扬镳——他们要赶回家加班,一个写工作报告,一个做PPT。
一周后,我又约一位体制内的朋友看话剧。看完后,我们就说再见了,因为她也要赶回去加班,看剧过程中她的手机仍然不停接收消息。
我的朋友们越来越忙了。这让我有点沮丧,因为我设想的朋友相聚,应该是坐在一起,不慌不忙,聊聊天,玩一玩。
当然,这不能怪我的朋友们,她们也无可奈何。那位未能如约而至的朋友在教培行业工作,最近,受“双减”政策影响,她所在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面临关停,她是一名HR,最近正忙着和员工谈解约。
写工作报告的朋友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她说因为疫情,公司经营困难,年终奖没了,她正考虑是否辞职。做PPT的朋友在一家国企上班,体制内的工作并不比体制外轻松。
这半年,周围朋友给我的感觉都是满脸倦容、疲于奔波,没有耐心去探讨更深入的话题,关心公共生活。这或许与快速变化的环境带来的动荡感有关,因为疫情,不少朋友工资缩水,被迫跳槽。
很多人被一种不确定感包围,期待更稳定、踏实的生活。这种精神危机在我们这些远离家乡、到一线城市奋斗的青年身上尤为明显。如果和家人住在一起,或许我们工作不顺利、心理上感到孤单时,回家后就顺口提了,但因为距离的阻隔,我会觉得,对父母诉说心事只会让他们徒增忧虑。
只能找朋友倾诉。但在一个忙于加班、见一面要花费1小时路程的城市,人们想维持深度的人际关系,获得友谊的支持,已经力不从心。缺乏深厚的情感支持时,人的漂泊感加重,快乐感大打折扣。
很多时候,我们投身于网络,是为了寻求快乐和外界的连接,网购是为享受拆快递时看到商品的新鲜感,刷短视频则是迷恋虚拟世界的热闹和喧嚣。我们还对工作抱有过多期待,放大工作的价值,因为这是我们在漂泊的生活中,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在其著作《工作的迷思》中提到,工作能够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气泡,“它会让我们将无穷无尽的焦虑不安集中到一些相对渺小、可实现的目标上来,它会赋予我们大权在握的感觉,使我们有尊严地感到疲惫。”
但如果工作过度侵入生活,我们将很难因为实现目标而幸福,而是沦为机器中一个齿轮,感受不到人的主体性存在。
是时候反思我们的生活了。今年,不少互联网公司宣布取消“大小周”,朋友说,有了完整的周末后,尽管偶尔加班,但她享受到了和男朋友去逛菜市场的自由。
在减少工作之余,我们需要回归日常生活,在大都市尽力构建小而深的关系,寻求精神的滋养。正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的,“要爱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要爱生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
我的朋友在这点上教会我很多。去年下半年,我去广州采访一位兼职说脱口秀的朋友,他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薪水尚可,经济压力不大。但工作的意义更多是糊口,很多时候,他需要扮演自己不喜欢的角色,陪领导喝酒,说违心的话。
为了丰富业余生活,他去看脱口秀,尝试讲开放麦。他每周讲两次,表演期间,将手机静音,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说,最开心的时候是站在舞台上讲笑话、尽情地做自己,观众给他鼓掌。
他所在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大多兼职,有编剧、学生、互联网从业人员。有一名主业是律师的脱口秀演员,业余还参加演讲比赛,组织律师朋友拍普法视频,生活安排得多姿多彩。
不久前,我参观了一个朋友的家。他在东六环边上租了一个空房,精心布置每一个物品,大到家电,小到绿植、墙画。
有些家居用品是在二手网站淘的,他因此交到了朋友。前几天,他去卖家那里拿凳子,两人聊起来,对方请他吃面,看他穿着人字拖,又送拖鞋给他。他也卖过窗帘,请买家来参观自己的家,一聊发现是同行,还有不少共同好友,相约一起去攀岩、游泳。
“真是美好的体验。”我的朋友说。很难说,这些关系是否能有更深的走向,但建立连接的过程,就是我们看见他人、感受生活质地的过程。我们也可以从微小的事物着手。比如,做一次手工、参加一次线下活动、拜访一位老朋友,在具体的生活中去感受个体存在的主体性。
对身处迷茫中的年轻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的建议是,多读书,构建自己的精神空间,同时也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方位,和世界形成一种“建设性的关系”。对此我深以为然,因为这能让我们看见自己在时代中的位置,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