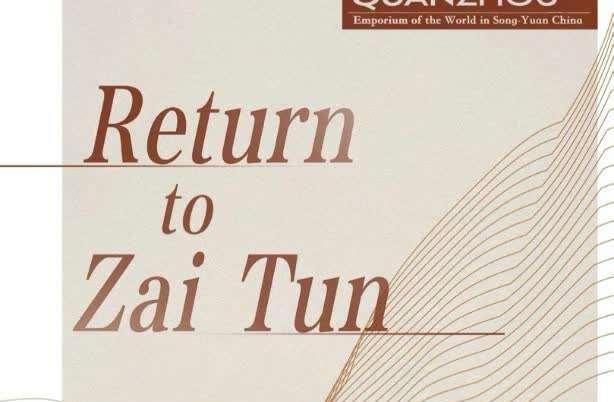从“社恐”到“社牛”,年轻人需要什么样的社交? | 周末谈
今年下半年什么词最热?“社牛症”绝对算一个。在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多人被打上“社牛症”的标签。比如奥运冠军陈芋汐,经常被人发现出现在别人的合照里,活泼开朗的性格便被人如此戏称;在真人秀节目中,某些受邀嘉宾“solo”全场、自嗨到停不下来的表现,也让头晕目眩的网友直呼其有深度的“社牛症”。
简单来说,“社牛症”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就是在社交时不畏旁人眼光,不怕别人嘲笑冷落,随时随地都能和各种人“social”起来。这种令“社恐症”们望尘莫及的社交能力,常常制造出一种“谁尴尬我都不尴尬”的奇异氛围。

“社牛症”为网友认知社交性格提供了一套符号系统。这个词流行后,很多年轻人突然发现,原来父母才是“人类社交的天花板”:比如有网友调侃父母走在路上突然就要唱两嗓;甚至有人讲出了“我妈买了只活鸡不敢杀,她提着鸡在小区里大喊问谁会杀鸡,让我拿了把菜刀跟在后面”的故事,令人忍俊不禁。
按照“社牛症”的定义,各种人都能被“塞”进去。不过,在其众多表现形式中,并非所有形式都那么可爱。有些极端形式过于“不走寻常路”,以至于令人生理不适。比如,有人在餐馆里突然高呼“童年的味道”,还有人会在别人用餐时“抢”走别人的食物。网上有不少所谓“社牛症”在地铁上练武术、在公交车上嗷嗷喊的出位视频。这些举动,无疑逾越了大多数人的接受界限。
与其说这些出位者是“社牛症”,不如说他们是故意哗众取宠,不分美丑地以极端行为吸引别人注意。这种歇斯底里的“一人饮酒醉”式卖丑狂欢,既会让当事人陷入“社死”,对其他人也是一种冒犯。这种行径和网友口中温和诙谐、欢快舒服的“社牛症”已经渐行渐远,失去了人际交往中的真诚和礼貌。

不少讨论“社牛症”的年轻人,都是以“社恐”的心态,来仰望、羡慕那些更具社交能力的朋友的。长期以来,“社恐症”早已受到心理学的重视和研究,不过,人们在社交网络上讨论的“社恐”,更多是年轻人的担忧与自嘲,未必是真的心理疾病。有些时候,“社恐”只是性格相对内向、“脸皮薄”的代称,未必需要纠正与治疗。
“社恐症”与“社牛症”的对比,传达出年轻人的某种社交焦虑。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联合对4000多名18~35岁年轻人调研发现,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交恐惧症。其中,有52.7%的人认为自己缺乏社交技巧,55.6%的人对自身条件不够自信,38.3%的人将社恐归咎于性格内向。那么,“社牛症”能作为解决“社恐症”的手段方法吗?“社牛症”能把社交的勇气传递给“社恐症”人群吗?
尽管两者在词义上存在互补关系,但想要让“社恐症”人群从“社牛症”身上汲取能量,难度却不小。有的人并非不能向“社牛症”学习,而是不愿轻易跨出“社恐症”的舒适区。对此,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陈曦在其论文中写道:“所谓的社交恐惧者们所排斥的并非是纯粹的交往,而通常是交往被赋予的背后的工具性质的目的,诸如日常事务的完成、工作关系的维护、工作技能的提升等等。他们渴望的,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交往,剥离工具性质的交往,抛弃各种目的化的导向。”从这个角度上看,屏蔽和反抗可能才是某些人“社恐”的缘由。这样也就不难理解遇见同事时赶紧低头扣手机或戴上耳机的“反侦察式社恐”了。

把“社交”这个词拆开看,它指的是跨越不同社群圈层的交际互动。每个人都有深浅不同的社交边界,想要获得的情感支持也是复合多元的,个体的一举一动都可能被别人贴上性格标签。过于世故圆滑或玲珑剔透的社交技能,虽然也可以称之为“社牛症”,但却未必能产生好的社交效果,反而可能给人留下聒噪、虚伪的印象。
在《倦怠社会》中,德国哲学家韩炳哲表示:“‘深度无聊’正是人类创造力所需要的,也是现代社会所缺失的一种状态。如果缺少那种“隔绝的本能”,那么人类的生存便成为一种烦躁不安、过度活跃的反应和发泄活动。”与其说当代年轻人愈发厌弃社交,不如说他们迫切需要能够安放自我、放下戒备的自我表露机会,需要质量更高的社交。
在“好奇心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中,超过六成的人都觉得“青春期的我们向朋友袒露心声往往能加深友谊,成年后这样做有时会适得其反”。人生在世,朋友和知己贵精不贵多。我们常常在对理想社交的想象中感到失落,缘分过浅、来去匆匆,或许才是年轻人真正的社交困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社交是人类生存的一种本能,如果“社牛症”的讨论热潮,能让更多人对社交有更深入的思考,这些讨论便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