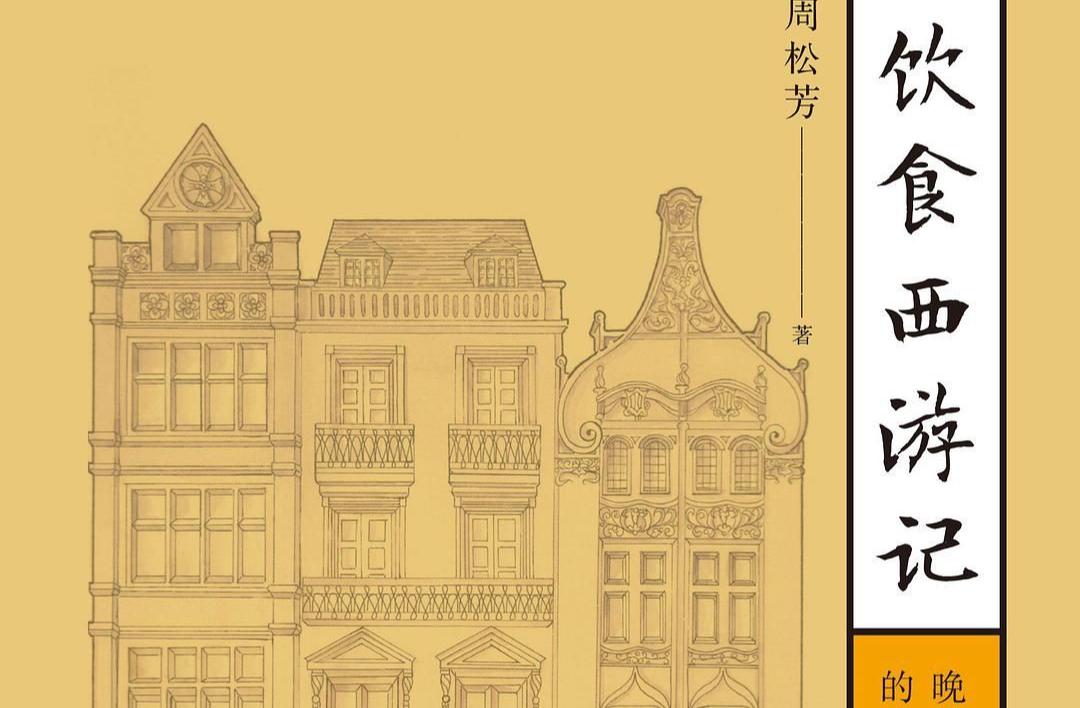阿彼察邦:贾樟柯就像那些了不起的制片人,给导演绝对的自由
6月12日晚上,第24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首场电影学堂活动(大师班)请来贾樟柯导演与执导了《热带疾病》《恋爱症候群》《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幻梦墓园》等影片的泰国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通过远程视讯,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谈。任教于上海纽约大学的著名电影学者、影评人张真则应邀担任主持人。

贾樟柯与阿彼察邦,一位写实一位梦幻,看似作品风格迥异,其实两人身上有诸多共同点。比如两人同岁,生日相差不到两个月;又比如两人都对故乡抱有深深的眷恋,并将其当做创作的最大灵感。而在最近公布的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入围片单中,两人的名字恰恰出现在一起:阿彼察邦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记忆》,正是由贾樟柯担任联合制片人。
对谈中,阿彼察邦导演坦承远行前的焦虑,表示自己生性内向,经过疫情中与狗狗们同住同吃的那段宁静岁月后,如今又要重新学习与人打交道。
而在经历了一场风波后,决定重回平遥的贾樟柯也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他表示,创办平遥电影展的初衷就是希望搭建好一个平台之后,让它自身得以良性运作,但目前尚找不到更好的团队来接手,所以自己还是当仁不让,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总是希望它能长得更健硕一些。对于筹备中的山西电影学院,贾樟柯也透露,目前还在硬件建设中,今年9月有望招生。他特别提到课程的设置,基础课会以纪录片为切入口,让大家了解什么是电影;而摄影课会恢复胶片摄影的教学,喜欢学生能在拥抱数码的同时,掌握传统的电影技术。
就在阿彼察邦即将启程前往法国的前一夜,两位老友追忆往昔,畅谈合作契机与疫情中的生活,并相约在平遥再会。
 贾樟柯(左)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通过远程视讯,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谈。
贾樟柯(左)与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通过远程视讯,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谈。
“希望通过作品表现电影和梦境的共生关系”
张真:你在泰国东北地区的孔敬长大,那里也是你发现电影的地方,能否谈谈这段人生经历。
阿彼察邦:四五十年前,在孔敬度过的时光,如今我依然记忆犹新,不时会回想起来。当年,我和当医生的父母就住在医院的家属大院里,医院就是我的游乐场,我对那里产生了一种依恋感——不仅指空间,也指飘散其中的消毒水等的气味。我的妈妈有很多医学方面的教科书,没事我会去翻阅。虽然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电影,但书里的图像,比如细胞、微生物等令我大开眼界,让我仿佛暂时脱离于生活的小镇,投身于更广阔的世界。我们的镇上还有一个大型的电影院,这也在我童年留下深刻印象。的确,故乡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在我成长的1980年代,我也很喜欢读一本科幻杂志,上面经常刊登一下现在堪称大师的科幻作家的作品,包括雷·布拉德伯里、阿瑟·克拉克、艾萨克·阿西莫夫,当时我称得上是科幻小说迷。此外,我的家乡也有悠久的民间故事的流传,尤其鬼故事那一类。因此,在我看来,科幻故事和鬼故事是并列的,无缝衔接的。
张真:你在拍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的时候,跑遍了泰国全国,请你分享一下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
阿彼察邦:那时我刚刚离开校园,我对一个问题很好奇:现实终于何处,虚构始于哪点。1990年代末期,中国台湾电影和伊朗电影对我影响很大,那些作品大多数是现实风格的,但能看出导演对电影的真相也抱有疑问。于是,结束留学生涯,回到泰国后,我决定拍摄一部低成本的影片。我在泰国各地旅行,还想出一个灵活的拍片方式——到一个地方就闷头拍,没钱就停机,等有钱了,再继续拍。所以,这部电影看上去就好像是有很多小故事拼接而成,其实是后期剪辑制作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令我得以探索虚构与真实的边界。那么多年过去了,甚至可以说,我已经不再相信电影,因为电影很容易就能被人操纵。然而,这点也是电影的魅力所在。所以,时至今日,我还是在拍那些神秘的故事;当年拍《正午显影》时的那些思考,依旧影响着我的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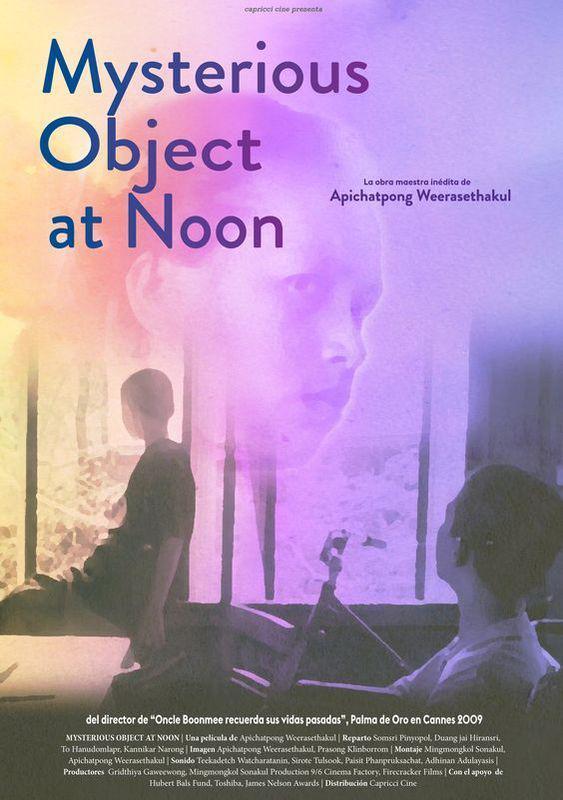 阿彼察邦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
阿彼察邦长片处女作《正午显影》
张真:我想谈谈你在家乡拍的《幻梦墓园》,其中的人物被梦境困扰,因此设置了一个治疗装置。事实上,你的电影常常带给观众梦境一般的体验,请问你如何看待梦与电影的关系?
阿彼察邦:说到《幻梦墓园》,这是一部可以从多种视角解读的影片。对我们泰国人来说,可能选择的视角就是政治或者象征主义,因为其中蕴藏了很多隐喻。当然,你也可以从纯粹电影的角度去解读。《幻梦墓园》就是我给故乡的献礼。你刚刚提到了梦境,在我看来,电影和梦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对话,而我希望通过作品表现电影和梦境的共生关系。我自己拍电影,就是在呈现一段梦境,或者说是一个我该做而没有做的梦。我还从科学的角度做过研究,发现做梦的生理机制和看电影的行为是很相似的——我们都需要一些虚构的故事来帮我们直面现实。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电影表达这两个世界有时会浑然一体,有时希望与黑暗是共存的,而后者可能是被一些非实体控制着,比如我们过去的历史。
 《幻梦墓园》中水的意象
《幻梦墓园》中水的意象
张真:《幻梦墓园》中有很多水的画面。事实上,湄公河经常出现在你的电影里,你还拍过一部《湄公酒店》。能否分享一下水的意象为你带来哪些灵感?
阿彼察邦:从中世纪以来,水就是人的象征,或者说,人是由水构成的。说到现实世界,水就是一个国家的血脉,把各个地区衔接起来。说到湄公河,它不仅衔接了泰国各地,而且北通中国,南达柬埔寨,把我们三个国家像一个整体连接在一起。但是,有时水也代表着割裂,比如割裂了泰国和老挝,而在当下,它也引起了一些政治争议。我还在不断地关注与观察,希望通过我的电影展现水的宝贵,呼吁各方都能做好沟通,为我们的后世留下足够的水。此外,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水是非常仪式化的。我的父亲过世后,我们就把他的骨灰撒在了故乡的湄公河里。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湄公河就是我的家,我会不断在我的电影里重现水的意象,它永远是我灵感的来源。
张真:电影之外,你也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创作。
阿彼察邦:对我来说,不论是电影还是艺术作品,它们都同属一个创作的世界,也都是自我表达的方法。但是,要拍电影的话,需要一个很大的团队支持;而艺术创作,或许我一个人就能完成,这给了我更大的自由。其实,艺术创作的过程跟我拍电影的过程很相似,我也会去实地勘景,也会去采访当地人,也会关注当下的局势,尤其是政治局势。参与两种创作的我的团队也是一样的。说到不同之处,拍电影更倾向于个人化的表达,而艺术创作满足了我社会性的需求。我想通过艺术创作来回答一个问题:泰国究竟是什么?
 《湄公酒店》中水的意象
《湄公酒店》中水的意象
故乡让人爱恨交织,有独特性又有普遍性
张真:我知道阿彼察邦导演最初学的是建筑专业,而贾导是学美术出身的。想请教一下两位,不同的专业学习背景对你们的电影创作有什么影响。
阿彼察邦:我从小到大都非常热爱电影,也一直想成为电影人,但是我生长在一个小镇,又身处泰国这样一个国家,最初不太有机会学电影。后来,我去曼谷就选了我第二喜欢的专业——建筑学。我发现建筑和电影有很多共通之处,比如都要对时间进行设计;都要让人物得以在空间里走动,注意这会引发他们的什么情绪。另一方面,导演和建筑师也有共通之处,都没法单枪匹马地完成工作,都需要一个团队紧密合作。我很高兴我学了建筑,在我看来,电影和建筑是相通的。
贾樟柯:我成长于中国西北部汾阳的一个小县城。整个县有四十多万人口,衔接着城市与乡村。其实,我一开始对于美术兴趣不大,为什么学呢?不是想成为艺术家,只是因为不学考不上大学。当时,我的数学成绩太差了,当老师的父亲就说,那你去考艺术院校吧。但之后学美术的两年过的过程,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今天回想起来,可能有两方面。
一方面在于,学美术之前,我对这个世界的构成是没有概念的,但当你开始学素描,你首先要从观察学起,这时候你就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当你再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光影,有明暗,有色彩,对我们习惯平面化视觉感受的中国人来说,观察方法会有很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学美术多少要学点美术史,也会逐渐形成一种思维方法,就是在媒体诞生普及之前,美术承担了很多其他功能,比如中世纪它讲述宗教故事,也有肖像画或者世俗的日常生活。一直到当代技术发展,特别是照相术发明后,美术的其他功能由新技术承担后,它才显露出它的本体,就是探讨绘画是什么。
这种境遇的变迁跟电影是一样的。电影在诞生之初,承担着记录新闻的工作。随着电视、网络的出现,电影的新闻职能被其他媒体取代后,就留下了电影的本质。我觉得这对认识电影性有很大帮助。
 阿彼察邦在《幻梦墓园》拍摄现场
阿彼察邦在《幻梦墓园》拍摄现场
张真:故乡在两位导演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请两位导演分享一下,故乡对你们的意义。
阿彼察邦:我对故乡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我很迷恋我对故乡的记忆,我在那里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也给了我很多做梦的机会。然而,正是这个故乡,也破坏了我曾经的一些美好憧憬。我了解到这个城镇其实存在各种苦难和政治上的操弄。比如孔敬是泰国曾经的一位总理的故乡,他是军政府出身,可以说是一位独裁者,直到今天,城镇的中心依然树立着一座他的纪念碑。我觉得这是故乡对我的一种背叛。也许我以后还会重回故乡,直面这座纪念碑,看看它什么时候会被拉倒。当然,我的故乡一直是我的灵感源泉,我希望能看到在那里长大的年轻一代对这个纪念碑有什么反应。随着年龄的渐长,我想我会很能理解其中的变化。
贾樟柯:从《小武》开始,我的作品大多数都在故乡展开,围绕着故乡构思,这跟我的情感方法有关。中国地域辽阔,每个地域都有它的个性,每个地方说话的方式、思维方式都不一样。我是山西汾阳人,我自己的情感处理和表达肯定是来自汾阳人的身份。从这点来说,家乡具有独特性。另一方面,这也跟我们身处这个变革的时代有关。小时候身处在一个小的封闭的城市,对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的想象,长大之后,四处旅行,才发现处于时代变革中的中国的中小城市其实都差不多。从这层意义上来说,家乡又具有能代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普遍性。
 《幻梦墓园》中的医院来自阿彼察邦对医院的记忆
《幻梦墓园》中的医院来自阿彼察邦对医院的记忆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与阿彼察邦故乡流传的鬼故事存在某种关联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与阿彼察邦故乡流传的鬼故事存在某种关联
《记忆》的契机与疫情的影响
张真:贾樟柯导演担任了阿彼察邦最新作品《记忆》的联合制片人。它是阿彼察邦导演的第一部英语对白影片,而且不是在泰国完成,是远赴哥伦比亚拍摄。影片入围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想请两位谈一下合作的契机。
阿彼察邦:跟贾导合作的想法具体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记不清楚了,可能是从《幻梦墓园》时开始的吧。在《幻梦墓园》的拍摄过程中,贾导尽情全力帮助我。这让我深深感动,因为贾导也是独立电影人,本来独立电影人筹资拍片都不容易,更不要说还要帮助另一位独立电影人,显然是难上加难。后来到了《记忆》,贾导就成了我的联合制片人。一开始,我是很紧张的,心想既然贾导来当制片人,我一定要拍好,否则太丢脸了。但合作下来,其实非常愉快——我这样说或许有点傻——贾导就像那些了不起的制片人一样,会给导演绝对的自由。我非常感激他,也很高兴能跟他合作。
贾樟柯:我要谢谢阿彼察邦,让我有机会跟他合作。此外,我也要特别感谢爱奇艺,《记忆》是我的公司西河星汇跟爱奇艺联合投资的。最初是阿彼察邦的制片人Simon Field给了我一个很短的故事和几张照片,我就已经非常喜欢了。能够在阿彼察邦的作品里出现我的名字,出现西河星汇跟爱奇艺的名字,我们都很开心。
张真:疫情期间,贾樟柯写了一封给全球影迷的公开信,名为《步履不停》。阿彼察邦导演也写了一封名为《“当下”的电影》的回信。经过了疫情的这段时间,你们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思考。
贾樟柯:我在疫情前有两个剧本想拍,疫情期间又写了两个剧本。但经过疫情之后,我最近处于思想的重组期,对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变得有些模糊了,我有些新的感受,但还没有明确捕捉到。本来是打算今年要拍一部新片,但我还是决定先定下来,可能要等到冬天才会开拍——我需要用一点时间把自己搞清楚。
阿彼察邦:那我迫不及待想看到贾导的新片。这次疫情一方面让我平静了下来,另一方面又给我带来新的焦虑。说平静,是因为那段时间我独自在家与狗狗们为伴,跟它们保持相同的生活节奏,这是新的人生体验。我通过它们的视角观察世界,发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那就是活在当下:狗狗们总是开开心心,毫不担心未来。说焦虑,是因为明天我就要远行,又要去见人了,而我其实很内向,两年不见人,现在又要重新学习如何与人打交道。然而,我实在很爱电影,所以我一定要去法国,去呈现《记忆》,之后我才能迈开下一步,去拍新的作品。我想,虽然我很爱我的狗狗们,但我还是更爱电影。
张真:阿彼察邦导演在曼谷创立了曼谷实验影展,贾樟柯导演创立了平遥电影展。两位在扶植年轻导演方面,都很有经验,能不能谈一谈。
阿彼察邦:曼谷实验影展是个比较小型的影展,目前在新的策展人的带领下,还在继续办。在我看来,年轻电影人最需要做的就是享受生活,享受当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别把电影捧得太高,不要把它当成一种宗教信仰,对它过于遵从,把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电影等同起来。不然,万一你不能成功,你可能会产生自我否定,感觉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贾樟柯:平遥也是“still going on”。我很享受跟青年导演合作的过程,我们有创投、有发展计划、有新片展映,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电影想象和崭新的电影世界。对我们这种从事了近三十年电影工作的人来说,很有启发。我很感谢平遥电影展,还有上海电影节,借由这样的电影节,我们得以看到年轻人的世界,有一部分是我们能理解的,但有一部是我们观察不到的。我想,这就是电影生生不息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