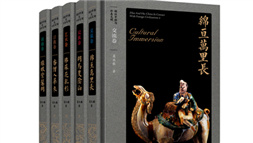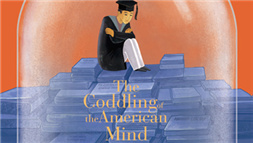7月18日傍晚,江西九江,三位江新洲农民在种南瓜。

7月9日,湖北黄梅,洪水退去之后,大河镇受灾店铺正在清理被损坏的货物。

7月11日,江西九江,前往江新洲抗洪的武警官兵在深夜完成任务后返回驻地,看上去有些疲惫。

7月13日,江西九江,周文斌把物品从一楼搬走后,烧掉废弃的杂物。

7月13日,江西九江,一位乘渡船撤离江新洲的岛民准备去儿子家暂住。

7月16日,江西九江,前往江新洲的渡口一座寺庙被淹。

7月17日,江西九江,江洲镇返乡抗洪村民程金保和他的老乡。

7月22日,江西九江,江新洲岛内仍有积水,积水深处玉米已涝死,积水浅处,玉米还活着。

7月22日,江西九江,两位江洲镇村民正在巡堤。
三个江新洲的农民在地里种南瓜,其实是在打赌——赌江新洲不会重蹈1998年的覆辙,赌洪水不会再次夺走他们祖辈开垦的土地。担心洪水涌入岛内的农民,提前掰掉地里尚未成熟的玉米,摘掉藤子上还没长大的冬瓜。
江西省九江市江新洲是长江中游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1998年洪水曾淹没此地4.2万人的家园。
今年7月,长江奔流至此已成悬江,水位最高时达22.81米,是1998年之后的最高水位,超警戒水位3.31米。水面比岛内的低洼地至少高出两层楼。
如今,洪水尚未完全退去。如果等警戒解除、洪水消失的时候,这里的农民会错过最佳的种植时令。如果播种后大堤决口,他们播下的南瓜籽,很可能在发芽之前就付诸东流。
2020年8月4日,在近90天的全球降水量分布图上,中国南方地区仍覆盖着一块极其显眼的紫红色。相比于2020年同样受洪涝影响严重的日本、印度、墨西哥等地,中国受灾面积最为广阔,大部分位于长江流域。
这些居住在长江流域的农民,已有人面临绝收。但还是有人在洪灾的阴影中播下种子。
入汛
迄今,中国入汛4个多月。紫红色区域已摆脱强降雨,但洪灾的阴影尚未消散。
6月11日,中国已有148条河流发生超过警戒水位线(简称“超警”)的洪水,中国全面入汛。但那时,一些与洪水有关的事并未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一位家住长江边的朋友说,他到7月才意识到,洪水来了。
洪水到来之前,没人知道它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降临。滞蓄洪区的人赌洪水不会逼开行洪的闸口,单退圩堤内已插秧的农民赌老天爷不会刻意刁难。山脚下的村庄想不到泥石流、滑坡会突然而至,水库旁的人们不会预料到溃坝的发生。千百年来的规律告诉人们,梅雨是会来的,汛期也是会来的。但洪灾何时来到,是一个未知数。
6月,江西宁都一水电站溃坝造成2人死亡。7月,在距龙归山30余公里远的一个村庄,水电站的一名50多岁的发电工说,汛期来临之后,水电站24小时运转没停过。出事的那天早晨,他冒雨去水库查看情况时,水库已经快要蓄满,发电机仍在工作。
汛期是水电站蓄水发电的大好时机,也是水利部门最担惊受怕“水库失事”的一段儿时间。按照当地的说法,今年汛前,宁都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下发的度汛方案要求“该电站空库运行,不能蓄水发电,同时加强工程巡查管理”。但事情并未按照“度汛方案”的原计划进行。
发电工的工资与发电量挂钩,发电越多,工资越高。正常情况下,这个发电站,每年可以发电大约400万度,1度电可以卖0.3元。直到6月5日下午,水库崩坝,发电机熄火。
附近的其他私营水电站在汛期来临之前同样未空库运行。另一家私营水电站的员工说,溃坝事故后,他所在的水电站才开始开闸放水。以前,水电站在汛期并不会放空,因为发电站担心雨季降雨一旦偏少,下半年很难再蓄足水发电。
龙归山的祖辈,也都曾依靠这河流与土地谋生。起初,他们在河滩开垦田地,在河岸修建房屋,用溪水喂牲口。后来,溪流被拦截蓄水发电,水库失事,洪水来了,人的“杰作”被不幸冲毁,灾难即成。这场灾祸的结局是,2人遇难,乡长与乡委书记就地免职,水电站股东与承建者共6人被依法逮捕。
在那场不过20分钟的洪水里遇难的是一对父子。他们在水电站下的一片河谷,依靠山泉水养石蛙。
龙归山不过是长江支流上的一个小村庄。长江会流经中国富裕的一些城市,也会抵达中国贫穷的一些村庄。汇水成江河,人们可以行船走舟,灌溉农田,人畜皆饮。
人们称其为“母亲河”,但是对生活在长江边的人来说,他们和江水的关系远不像和母亲那样简单。当长江水超过一定的水位,水就变成了洪水。
在鄱阳湖区,水质和低廉的地租吸引来养珍珠蚌的人。但在2020年洪水侵扰下,他们不得不以每天抢救几十只的速度,试图挽回洪水深处20万只珍珠蚌。做秀珍菇生意的人,在1998年被洪水冲毁的房屋空地上建起大棚,每到夏天就开始对洪水提心吊胆。
当然,生活在洪水阴影之下的远不止长江流域的人们。当7月下旬雨带北抬后,淮河流域开始有洪水出没,以至于“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不得不让洪水进入蓄滞洪区。其实淮河上游地区7月之前刚历经大旱,靠人工浇水而得以成熟的瓜,在持续的暴雨中腐烂;一些几近干涸的龙虾田,又面临被洪水淹没的窘境。
悬江
人们把抵御洪水的希望,寄托在堤坝等各种水利工程上。
江新洲大堤的加固工程今年洪水来临前还在进行。岛上江洲镇九号村村民赵芙蓉在跟着工程队修大堤的护坡。6月下旬,她看着长江水离岸越来越近,水位一天比一天高。前一天她还可以在护坡上一排砌10块六角砖,第二天只能砌8块,后来是5块,直到凶猛上涨的江水逼停这项工程。
这里靠上游10公里处九江水文站的数据来观察洪水的踪迹。7月5日,九江水文站水位超过19.5米,这是江新洲的警戒水位线。这个敏感的数字出现前几天,江新洲就召开了防汛动员大会,开始准备防汛物资。接着,各村安排防汛队为抗洪做准备,有经验的岛民临时组建起抢险队,41公里堤岸上的171座哨所里村民24小时驻守。
用农民的话来说,江新洲的地形“像一个盆”,四周高堤环绕,堤外是洪水,堤内是田舍。九江水文站的水位每上涨1厘米,都悬在村民头上。
撤离通知在水位超过警戒线3.31米之后紧急下发。那些还把蔬菜种在岛上的农民,只好把原本可以长到30斤的冬瓜在15斤的时候就摘掉。
两位老人怕洪水来了把自己养的鸡淹死,抬着鸡笼登上了渡船去九江市;另外两位老人则把自家50余只鸡的双腿系上绳子,和家具一起安置在二楼,以免飞走。一个小女孩儿坐在三轮车里被爷爷、奶奶推着去坐渡船,他们带着青椒、豇豆、干豆角准备去市区的亲人家避险。
紧急撤离出现了新的生意,比如帮老人家拆掉一楼的空调搬去二楼,就可以赚到200元;因搬家而扔出大量废纸箱,有人捡了两三个小时就卖了200多元。
密密麻麻的蚯蚓从洪水中的堤岸里逃出来,爬过人们抢筑的沙袋,在堤面上留下痕迹。太阳出来,还没钻进土里的蚯蚓就被晒死了。洪水来时,蛇也多了,晚上巡堤的人总能遇到。
岛上有农户家的三只羊,被淹死了。近年来小岛上用于发展旅游业的油菜花与芍药园,也都被淹,就连小岛上供奉海神“妈祖”的天后宫也难逃一劫。
有人对洪水不甚在意,两个住在地势较高处的老人说,他们不愿意撤离。“1998年那会儿都没事儿,堤破了洪水淹过来也要二三十个小时,到时候再撤也来得及。”
超警的水位让另一些小岛居民惶惶不安。
52岁的农民周文斌在江新洲以300元/亩的价格承包了600亩田地,现如今地里种着黄豆、水稻、玉米。
往年这个时候,他本该在地里给黄豆打药,可如今,洪水来了,他无事可做,只是坐在家门口打苍蝇,或者跟年过古稀的叔伯聊天,频繁地看手机上九江水文站的水位。烟头扔了一地。
他家将近一半的农作物被内涝积水淹没,另一半未淹的庄稼地因为积水拦路无法进入。他还在纠结,是否要给尚未完全淹没的庄稼打药。打药的机器根本下不到地里,而用无人机打药的成本又太高。好在他早上涉水去查看时,黄豆叶子上暂未出现虫屎或有被虫啃食的迹象。
往年在秋天才来收黄豆的河南商贩,提前打他电话询问受灾情况,想看看今年黄豆收成如何,好判断到时候要不要来江新洲。而周文斌几乎每天都去地里看一眼,一天比一天确信,自家地里尚在花期的黄豆要绝收了。
内涝半月,岛风里已有物体腐烂发臭的味道。一些黄豆苗、玉米秆、花生秧都烂在了地里。
往年他并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庄稼被淹两三天没什么大事儿,江新洲上有23座机械排涝站,很快就能把积水排到长江里。但7月以来,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两三百亩庄稼在水里泡着,却无能为力。
“长江(洪水)水位太高了。”周文斌说,“排涝站的泵停了,积水出不去。”自6年前在这里种地以来,他还没有遇到过类似惨境。今年遇大涝,他估计要损失十几万元。
7月18日傍晚,周文斌跟村中老人闲谈时,一位带着铁锹的男人从他家门口路过,告诉他“园林洲(堤段)在渗漏,田里进水了”。水位已超警13天,他当即决定骑车去堤上看看,因为渗漏是一种危险信号。
“就是怕他这个高水位持续时间长。”一位九江市柴桑区水利局的干部站在大堤上表情严肃,“洪水要是找一个口出来之后,咔咔咔全涌进来了,把(大堤)中间洗空以后形成一个空洞,空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果便是决堤,岛民对此心知肚明,却不敢胡言乱语。江水不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周文斌的心就一直悬着,他与老天爷的对赌就还没分出输赢。
空了
百余年来,周文斌和他来此开荒的祖辈,与长江大大小小的洪水交过许多次手,1954年、1983年、1998年、2016年……有时候洪水很快消退,有时候两者会僵持许久。轻则冲破岛民筑起的江堤防线,重则冲毁房屋、农田,甚至带走生命。
岛上的老人,见证了江新洲上越修越高、越筑越牢的大堤。人们如今严防死守的北堤,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岛民们一担土一担土挑起来的,他们也因此拥有更多的土地。
“这个堤是人造的,洲也是人造的。”曾做过村干部的程金保站在北堤上,指着堤后长满庄稼的田说。他还记得父亲在江船上当水手时,船会从如今已是一片芦苇荡的地方驶过。那里属于曾经的长江,如今属于岛民。
长江水成就了江新洲,但也在1998年8月4日无情地扫荡了它成就的一切。
那一天的21时15分,江新洲大堤在被洪水浸泡39天后溃堤。洪水用了约30个小时淹没岛内1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庄稼绝收,4.2万人受灾,很多人瞬间变得一无所有。
洪水还冲毁了岛上2000多栋房屋,后来更多的房屋建在堤上,堤身挑土抬高,盖起的一楼不住人或者只是用几根柱子把楼房撑起来,避免洪水来时被泡。1998年的洪水,还淹了岛上所有的坟墓,后来程金保特意动土,将祖坟迁到附近比公墓高一米的地里。
1998年后,在江新洲南侧河道里一个叫官洲的小岛上,2000余人移民上岸,把那片土地还给长江,不再设防。而如今小岛江新洲正用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为大堤修建一堵33.7公里长的防渗墙,34.1公里的护坡,20.46公里的防浪墙。
那场洪灾催促岛民洗脚上田。在等待洪水退去的日子里,有人尝试着走出小岛,去城市做木工或泥瓦匠。
1998年之后一直待在岛上的周文斌,起初只是跟着表哥卖化肥。随着更多的人离开小岛,他们的化肥生意越来越难做了,“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种地”。
“江洲第一批人离开是在1998年溃堤后,之后的每年都递增。”程金保2004年离开江洲镇去九江工作时,小岛正涌起第二拨儿外出务工的热潮。在岛上,夏天连到江里游泳的人都变少了。曾经的产棉大镇,因为没人种棉花,轧花厂也倒闭了。
进城务工对于农民的吸引力,已经渐渐大于种地糊口。村子在过去的22年里渐渐“空了”。
不愿意出门打工的周文斌,趁机开始承包那些外出务工者的土地——一个没种过地的岛民在年过四旬的时候开始务农。他种的地慢慢从2014年四五十亩扩大到如今的600亩。妻子张品红其实并不想留在岛上,至今仍有些抱怨丈夫当初的选择:“跟同龄人相比,我显得老很多。”
她指着门前一排建在屋脊上的楼房说:“这一排我是最年轻的。”她今年47岁。除了过年时,往日里那些楼房大都紧闭门窗,四野空旷,夜晚除了仅有的几家亮着灯,这个村庄一片漆黑。
她和丈夫成为小岛上为数不多的“年轻人”。
当2020年洪水到来时,小岛的“空心化”让江新洲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拥有3.6万户籍人口的江洲镇,在家常住的只有7000余人,实际可用劳动力不足1000人。
更多的是留守老人与妇女,实际上岛上连老人都在变少。堤坝上盖起的房掩饰不住村庄的衰老,年轻人多数在九江市买了新房,人们在岛上见到更多的往往是葬礼,而非婚礼。岛上一所小学的校长眼睁睁看着岛上的学生从五六千,减少到200人左右。
这并非只是某一个村庄的状态。7月以来水库溃坝的龙归山、发生山体滑坡的袁山村、鄱阳湖区那些受灾村庄,都类似。
7月10日,江洲镇在洪水暴涨时,发出《致江洲在外乡亲的一封信》。一位在堤上参与抗洪的岛民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场景,那封信发出的第二天,渡口等待过江的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小轿车一度排了约4000米长。此后几日,平均每天1000余江洲儿女回岛抗洪。虽然其中很多人早已从江新洲搬离。
然而程金保发现,这次返乡的大部分人,多数是1998年抗洪的那一批。22年前他们的年纪与如今站在堤上的军人差不多,但22年后上堤的年轻人并不多。他担心的是,再过20年,岛上谁来守堤?
当今年的洪水退去之后,像他这样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将再次离开,岛上“又只有寥寥无几的老人”。
7月30日,九江水文站水位已经降至22米以下,岛上准备排涝。
洪水渐退后,因洪水撤离的群众开始重返家园,但长江流域仍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时期,监利以下江段水位仍处于全线超警状态,淮河、太湖水位也呈退势。关于洪水的消息,正在变少。
九江水文站至今超警已逾30天,江新洲大堤上,仍有岛民提心吊胆地巡险。江新洲大堤还算安全,堤内积水开始慢慢消退。小岛上,有老人乘渡船归来,有老人把被子抱出来晾晒,有老人在屋檐下搓玉米粒儿,也有老人正在参加一场葬礼。
周文斌又去地里看了看,黄豆苗已露出水面,但叶子已经烂掉了。等积水全部消失的时候,想补种也过了时令,只能等到10月份种油菜和小麦。闲置的8月、9月,如果地里实在没什么事做,他们要考虑出门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