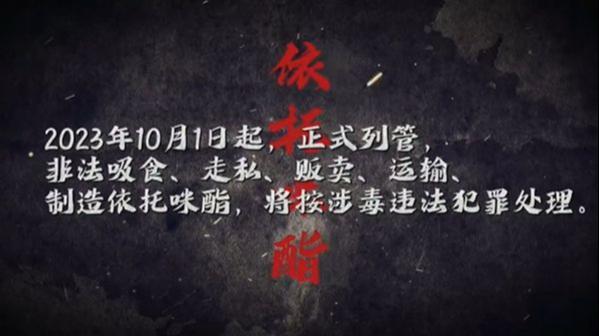关于爆款音乐剧《大状王》,你想知道的都在这里了
过去一个月,喜欢音乐剧的你也许没有“打飞的”赴港看《大状王》,但很有可能在朋友圈、社交平台刷到过《大状王》。“断层的好”“华语音乐剧标杆”“六边形战士”……不管是从业者还是普通观众都交口称赞。好多戏剧爱好者甚至连日蹲守网站,哪怕剧场只剩下面向特殊人群的福利票,也抱有一丝希望最终在无人购买后变回普通票的机会。
是什么样的新剧具有这样的魔力?本报独家访谈作曲、编曲及音乐总监高世章,作词岑伟宗,编剧张飞帆以及导演方俊杰四位主创,请他们复盘这部作品的台前幕后。希望借由这样一篇报道,窥见这部历时八年磨砺出的舞台爆款所走过的历程。更希望从业者可以从他们的创作分享中,总结参考华语原创音乐剧制作的经验得失,为本土音乐剧的原创力量发展,形成有益推动。

【嘉宾简介】
高世章:《大状王》作曲、编曲及音乐总监。曾任张学友音乐剧《雪狼湖》国语版音乐总监。参与创作粤语音乐剧《四川好人》《白蛇新传》《顶头锤》。此外还参与《如果·爱》《投名状》《捉妖记2》等多部电影配乐创作。
岑伟宗:《大状王》作词。在音乐剧、电影、电视及流行音乐均有涉足。兼任编剧及作词的作品包括《阿飞正转》《穿 Kenzo 的女人》等。担任音乐剧《四川好人》《白蛇新传》作词。《十字街头》(《如果·爱》电影插曲) 作词。
张飞帆:《大状王》编剧。编剧兼任作词作品包括音乐剧《一水南天》《时光倒流香港地》《热斗狮子球》《一屋宝贝》等。
方俊杰:《大状王》导演。现为香港话剧团助理艺术总监。执导作品有《大象阴谋》《暧昧》《结婚》、高世章策划香港原创音乐剧音乐会《我们的音乐剧》等。

一
情缘起
《审死官》妙改《大状王》
文汇报:《大状王》历时八年,最终同观众见面并在华语地区产生热烈反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部剧的诞生过程吗?
岑伟宗:那是2015年,我同高世章两个人去上海看戏,一天下午五点多,我们坐在咖啡店,我喝咖啡,他喝水。然后突然之间我就放出一个idea:“我们把《审死官》这个戏变成一个音乐剧好不好?”高世章马上反问我一个问题:清代的音乐是怎么样的?我回他,这个我不知道,你可能知道。(笑)
要令这个想法成为现实,那就需要找一个厉害的编剧,来丰满完善故事情节。所以我一回到香港就打电话给张飞帆请他写一稿提纲,加入主创团队。但是我跟他也直说,目前这个项目还没有投资方,就只有我们两个(高、岑)哦。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下来。
仅仅过了几个礼拜,飞帆就把故事大纲交给我。令我们很惊喜的是,除了故事中几个角色名字跟《审死官》有点关系之外,基本上完全是一个全新的故事。看完之后我们觉得这很有潜力,虽然故事对于音乐剧呈现来说有一些复杂,但好的剧本基础让我们完全有信心可以发展得更好。

随后我完成了一个六页的项目策划,放在抽屉里。接下来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投资人制作方。同年十月,我在新加坡看戏,碰到时任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的茹国烈先生。他询问我手上有没有合适的项目,一听说是基于《审死官》发展而来的故事就很感兴趣。尽管当时西九文化戏曲中心还没有正式落成,但考虑到因为《审死官》既有粤剧也有周星驰主演的喜剧电影。那么在西九戏曲中心演出这样一个音乐剧,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会很有意义。
把这个合作意向落地的过程中,高世章就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是否可以不同于以往香港做音乐剧的模式,而是从读剧(剧本围读)、工作坊(Workshop)、预演再到正式演出,一步一步去发展这个项目?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从2015年开始慢慢打磨这部戏。2019年预演后收集很多观众回馈然后再重新修改,原本计划2020年上演,由于全球疫情影响直至2022年才与观众见面。而在这一版的基础上我们后续又有不少调整,这才有了今年年底和观众见面的《大状王》。

高世章:其实在《审死官》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另外一个传统戏曲剧种的保留剧目来改编音乐剧的可能性。相比之下,《审死官》可以在粤剧以及电影两方面,带给不同代际观众不同的联想,这让我觉得很有趣。不过我们从一开始并不打算在两者基础上做改变,而是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属于自己的版本。因为我、岑伟宗、张飞帆以及方俊杰都是老搭档,合作过很多剧目,所以我相信我们一起“天马行空”一定是没问题的。
二
凭栏处
西洋剧化变中国戏
文汇报:那么从《审死官》到《大状王》,故事具体有着怎样“天马行空”的变化?背后有着怎样的考量?从2019年到2023年,《大状王》经历了很多次大幅调整。有哪些改变?又是为什么?
张飞帆:岑伟宗约我写剧本的时候,最开始就提了三个要求:第一是做清代戏;第二是虽然是做《审死官》,可是不要像电影《审死官》;第三是想做“救赎”命题,类似中国的《浮士德》。接到这个案子,我就回想我们小时候看《审死官》,周星驰演的状师宋世杰其实是一个虚构的人物。而历史上清末广东有一位真实的状师名叫方唐镜,他经常在粤语文艺作品里以反派形象出现,有一点像黄飞鸿故事里的 “奸人坚”,这种戏剧人物组合其实是十分具有香港本地文化特色。那我就想如果写《审死官》为什么一定要以宋世杰为主角,我可不可以写一个“坏人”?或者写一个“坏人”最终为何变成“好人”的故事?
最后我选择用方唐镜讲述一个要从坏人变成好人,最后要去救多人的故事。因为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所谓“道”、所谓“天理”的话,那么坏人终因得到审判,那么我希望他是通过自己的牺牲去拯救更多人,来完成救赎的命题。
剧本初稿的故事人物比较多,人物关系也比较复杂,也有比较大篇幅因果的内容。但对音乐剧来说并不完全适合。所以这八九年间我一直在修改调整,可以说2015年的故事大纲到2019年预演,有非常大的改变;而2019年到今年呈现的版本,又经历许多变化。

岑伟宗:我们仅仅在排练时期已经有20多稿的修改,但其实所谓的“一稿”又不仅仅只是“一稿”。
文汇报:对当下华语原创音乐剧的创作来说,文本故事一直亟待突破。在此前的音乐剧创作中,张飞帆写过不少香港本土故事,比如《一水南天》《热斗狮子球》,也尝试过海外音乐剧的本土版本,比如《一屋宝贝》,都有不错的反响。在写音乐剧故事,尤其是香港本土故事时,您有怎样的经验可以分享?
张飞帆:尽管有人说音乐剧故事要简单。到了这个戏,我会思考是不是音乐剧只能简单、只能首要考虑娱乐性?我想用《大状王》的故事改变这种认知,令大家觉得音乐剧也可以有人文关怀。所以这部剧我们花了八年时间去努力提高它的艺术品质,让观众觉得在娱乐之外,也可以有回味和思考的空间。我想这也是现在很多观众回馈看了三次四次的原因。因为每一次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第一次可能是歌很好听,第二次可能觉得故事很有意思,可能第三次就是会联想,自己的人生又是怎样的。
说到写香港故事,我觉得作为一个编剧他很难去写他不喜欢的东西。那我喜欢的东西恰好都是跟香港本地有关系,我写的香港故事都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都是在表达自己,所以自然而然地就会流露非常本土的气质。
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故事就只能面向本土观众,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首先香港有很深的中华文化底蕴,同时我们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文化交汇融合,这也是我们能够创作出这样一部音乐剧的文化基础。不管东西文化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找到“追求真善美”的共鸣。

文汇报:那么想问高世章,您最初那个疑问——清代戏音乐什么样,最后是怎么在创作中“自问自答”的?全剧音乐带给观众印象最深的一点是音乐元素的丰富性,从佛教音乐到粤语本土的山歌、南音、数白榄,更不必说音乐剧作为西洋艺术所本来有的各类流行元素。您是如何将这些元素杂糅统一的?
高世章:关于“清代音乐什么样”的答案就是“不要想太多”(集体笑)。如果我们要做历史剧的话,那肯定要围绕清代做很多研究。但就音乐剧来说,清代作为时代背景虽然要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设法令这个清代角色如何跟现代的我们连接起来。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什么时代做什么音乐,那对音乐剧来说就比较死板。就好像电影原声,比如西方18世纪的故事,它的配乐也不是当时的音乐,而是现代人演绎那个时代人物的心境、感觉。这个戏有很多的人物与不同的情节,而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面向,这就使我可以放很多不同的音乐感觉进去。人物心境怎么走,我的音乐就跟着怎么走。我相信看过的观众不会觉得现在的音乐对于这个清代故事有违和感。
而关于“音乐元素风格杂糅”这个创作手法来说,其实在上一部港话音乐剧《顶头锤》就有了。不一样的是,《顶头锤》故事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的香港,是我们当代人相对比较熟悉的年代。而《大状王》的时代背景更久远,所以就可以融入更多音乐上的想像。
而风格多变的另一个考量是,我会想哪些东西可能观众听过,但没有想过放在这个故事里是什么样,希望可以有一些“异己感”突显出来,《大状王》的这个野心可以说是较《顶头锤》更进一步,不过理念上则是一以贯之的。
三
行路难
精雕琢方显玉温润
文汇报:说到八年间不断打磨,不断修改调整。我就听到一个故事,说作曲几乎是在最后期限(Deadline)前一天经历了大改动。那牵一发动全身,音乐剧音乐一旦改动,歌词要配合改,舞台上的编舞、调度等等都要跟着变。能跟我们说一下如何下定这样一种决心,又是什么原因觉得“非改不可”?
高世章:2019年我们预演以后发现在说故事、音乐,以及观众接受程度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回头看我觉得2019年的版本比今年这个版本更有野心,我们想做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可能野心太大了,观众也接受不了。就拿第一首歌来说,在预演中,就有观众回馈唱得太快了,歌词密度太高听不太清。这其实是因为我在创作中预想的是另外语言来演唱,当时自己觉得没问题。我自己也纠结很久,到底改还是不改,我很想不改的(笑),但是最终观众的回馈就是不能太快。所以最后我就重新改变了节奏,改到观众能够听清歌词为止。
不止这一首。如果和2019年相比,不管是情节还是歌曲都改了一半以上。本来2020年可以演出,但后来因为疫情关系延期,对我们来说正好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慢慢修改打磨。就是即便没有观众2019年的回响,我们每个人也都抱定了要不断修改的想法,刚好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把这个作品一点点弄得更好。其实改东西是我最喜欢的。直到现在演出后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要改,他们都劝我说不要再改了已经很好了。(笑)

文汇报:那对填词来说,如果要改一半的曲子,歌词就要跟着重新修改“返工”…
岑伟宗:这没什么争议。这是我们工作的本分。改东西是他的习惯,那作为老搭档我就跟着他走。反而我们需要在意的是,讲清楚为什么要改,只要能说服我,这反而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舞台艺术是一个团队。改或者不改虽然是一个团队集体的决策,但我们有一个信任的前提是,我们彼此对于对方做的东西非常熟悉和了解。比如方俊杰在进场排练前,一定会把高世章做好的音乐demo带每晚上听个二三十遍,听到对每一个音符都非常熟悉,才能了解到他音乐每一处的用意,才有把握知道在舞台呈现上哪些需要放大,来让音乐更加出彩发光。在这个前提下,假设是方俊杰提出要改,那也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理由来说服我们,而我们因为对作品由了解,也能很快理解他说的意思,那么这样的修改交流就很顺畅。
方俊杰:很多人问我们创作过程有没有过吵架,我们真的没有。因为我们合作很多次,对彼此非常了解,交流修改意见本身就是一种创作思想火花的碰撞。
我觉得我们四个都是不怕要改变的主创。因为好的东西都是改出来的。因为一个人提出要改,绝对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看到了问题。这样只有越改越好。好的作品很多时候都是改出来的,如果你害怕去改变的话,那对我们主创来说就很难进步。其实19年预演后的这几年,我们没有放下这个项目,说的最多的就是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更好。就在开始访问之前我们还在谈,如果下一次再做,还有什么需要做的。对我来说,艺术没有完美的一天,永远可以做得更好。彼此艺术火花的碰撞其实是我最快乐的时刻。如果没有这种火花,创作其实也会很孤独。

高世章:音乐剧导演对音乐的敏感度是很重要的。除了在做功课以外,他一定要了解为什么音乐这么写,这里为什么要用这个段落、乐器跟速度。每一个步骤也是很重要的,那如果是每一步都要作曲告诉导演,我为什么这样做,很费时间精力,也很难碰撞出更出彩的舞台呈现。所以音乐敏感度是音乐剧导演非常重要的本职与素养。
文汇报:从观众回馈看,这次《大状王》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词曲贴合度非常高。我们知道诞生于欧美文化的音乐剧,其音乐创作语法为自然更适用于英语。那么非英语地区如何克服语言障碍,带给观众词曲浑然天成的体验?这是否需要反复的词曲调试与磨合?
岑伟宗:在我创作粤语音乐剧伊始,听到过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粤语做音乐剧很难,写不了的。而还有些人则认为,如果用粤语做音乐剧,可能会受到语言理解限制很难走出粤语地区。但是几年前我们把《顶头锤》(香港话剧团出品的另一部原创音乐剧)带到北京的时候,观众通过字幕去理解歌词内容,一样很享受观演过程。甚至有观众觉得,就应该由粤语唱。
这两种声音让我意识到,其实语言是工具,它最终还是跟用的人有关系。
而如果要说普通话写音乐剧歌词有什么难点,那么我想,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就是普通话里有很多同音字、近音字,如果不注意这一点,可能在实际演唱时造成理解上的多义性,对观众理解来说就有些难以辨别。
但不管对于普通话还是粤语,如何打破“不能演唱”或者“很难演唱”音乐剧的偏见,或许现在正是我们探索这个答案的时候。
高世章:就我自己的工作习惯来说,通常是先写了曲,然后再请拍档填词。不过这并不是一次就结束的。因为英语的话我大概可以预先感知如果想改词义,大概会改成什么单词以及它的发音,从而也就能注意音乐在与歌词音调匹配的问题。但是粤语和普通话对我来说要改的情况比较多。因为这两者带有音调,如果要改词义,那么词语音调的变化对我来说会比较大,那么就需要重新去匹配更合适的旋律。那么如果我们觉得歌词那个意思到了,但是听起来不那么顺耳,那么哪怕这段旋律我写得自己很满意也一定要改。
那么这是不同语言对我创作上的差异。在这之外,我觉得做音乐剧最重要的是要“讲故事”。我写出来的音乐,会交给几位主创来判断。一定是要到他们说“我看到了那个画面”,而不是“我听到了那个音乐”才是对的。音乐剧的音乐不同于流行乐或者其他样式,它不单单是要好听,而是要让音乐自己讲故事。甚至于没有歌词表意,大家也能结合戏剧上下文语境大概了解是一个怎样的感觉。这是我觉得创作中值得分享的一个经验。
四
应知我
承传统砥砺谋破局
文汇报:我了解到这部戏在制作模式上与此前的港产音乐剧有很大不同,具体跟我们聊聊是具体过程以及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吗?
岑伟宗:以往我们的音乐剧制作很多都有一个具体的“Deadline(最后期限)”也就是公演日期,大家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创作排演。这一次世章说希望不要考虑最终的上演时间,而是一步步从读剧到工作坊再到预演公演,呈现在观众面前。
确立这个理念之后,世章、飞帆和我三个人先在西九文化区的办公室读剧很多遍,然后才开始邀请导演参与,后面有了2019年的预演。而预演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很明确,这是一个初步的状态,而绝对不是最终的呈现,是为了听取观众的意见对作品进行修改和提高。
文汇报:其实这也是百老汇、伦敦西区做音乐剧的模式。
高世章:没错,因为我早年有过在海外做音乐剧的经历。但是在香港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资源有限。所以通常都是先定剧场的档期,然后倒过来定创作週期,写剧本多久,写音乐多久。所以很多人找我写音乐剧就会问,你写音乐剧要多少时间。我其实很难回答一个具体的时长。
当然我们几人在香港做音乐剧也做了很多年,对这样的模式很熟悉适应。但《大状王》让我觉得是一个机会,改变对香港舞台、香港音乐剧、尤其是香港原创音乐剧的一些看法。让香港本地观众、让内地观众通过这部作品了解到香港的音乐剧发展到了什么地步。其实不只是在香港做音乐剧并不容易,我相信即便在内地音乐剧发展基地——上海,也会面临类似问题。作品很多,但每部作品的制作时间不一定够。尽管制作周期与作品品质不是完全相关,但时间一定是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对音乐剧这样一门综合艺术而言。

岑伟宗:对我来说最开始并没想到让《大状王》的制作模式成为后来者的参考。只是说如果要做一个好东西,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时间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把握更多的时间,在创作阶段就把这个项目做好。而至于后面怎么样,那就要用作品来说话了。
复盘这个项目,我个人学到的两点是,你要做一个项目投放市场,你的目标如果是要吸引最多的观众来看,那么就一定要在创意之初就把观众因素考虑在内。比方《审死官》这个既有粤剧传统文化、高雅文化的底蕴在,又有周星驰电影这个流行文化的影响力在,那么它天然就有一个观众基础。
而我学到的第二件事是,一旦抓住一个有趣的创意,怎样去找到突破口、怎样找对的人来把这个创意实践好。
举个例子,“公堂戏”在粤剧里有,但是音乐剧里好像没有。那么如何用唱来表现公堂辩论,既要把词唱得清楚,然后又要给观众行云流水的感觉,其实难度很大。难度大也就意味着,一旦能做好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从艺术上来说也会让观众产生兴趣。作为主创,我也会觉得这个挑战很有意义。

文汇报:回溯香港音乐剧的发展历史,从上世纪70年代的《白娘娘》,就集结罗文、黄霑等一众顶尖本土文艺人才,拥有很高的起点。而早在1997年就又出现了张学友领衔的现象级音乐剧《雪狼湖》。但近年音乐剧虽然品质不俗但很难有如此大量级作品,几位如何看待当前这种状况?
张飞帆:放眼整个中国甚至亚洲音乐剧行业,香港地区发展较早。高世章说香港地区音乐剧发展了50多年。而我也注意到,韩国同样起步较早,但他们在过去2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实现了产业上的超越。那我会想,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能不能用这50年的经验,去出产一个顶尖水准、代表香港音乐剧的作品?带着这个目标,我们想用《大状王》向中国本土观众、向全世界说,我们可以用心做出什么样的作品。我不是想要标榜这部作品有多好,而是用这部剧从制作到最终呈现,带给大家一个希望——“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可以继续做更多好的作品奉献给观众。”
方俊杰:在我看来,过去20年韩国发展音乐剧以及他们的文化创意产业,所用的方法是“用数量去带动品质提升”。就是用大量的资源投入,集纳尽可能多的人参与。那么在发展初级阶段,较之追求品质,更关注产业体量,依靠量变引发质变。可是这套模式,如果照搬到香港地区,恐怕是行不通的。
除了人才资源等问题,在香港很多音乐剧只能演四五场。这也就意味着,刚开始演出几场,听到一些回馈声音,好像刚懂怎么去修改怎么去提高的时候,作品演出就结束了,很少有机会去修改提升再重演。可好的作品是改出来的,要给到主创足够的时间沉淀和思考。我们《大状王》这一次很幸运有机会从预演到首演再到重演,作品一步步提升,收获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不过,当下愿意投入这么多资源的机构不多,因为音乐剧不是一个小的投入,更何况是持续八年的一个演艺项目。但我们这次的经历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个信心,投入更多来让作品不断成长,这样做是值得的。
张飞帆:我和方导演都是出身于80年代的香港人。我们出生的时代,是香港文艺的黄金时代。我们出产的电影、电视剧、粤语流行音乐风靡整个亚洲。那其实音乐剧就是一个综合戏剧故事、音乐表演的艺术,而这些恰恰就是我们曾经擅长的东西。那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出好作品的。这一次可以说是把我们相信的东西一步步努力变成现实。
高世章:音乐剧如何从一部一部的作品,变成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产业?这是很多地方都在努力的事。那目前我们看到上海就正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既有一些艺术水准较高的作品,但也确实有更注重商业效益的产品。因为即使不把品质做到最好,我们会发现,还是有很多观众因为文化消费习惯去看。那么对于香港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年我们更多的音乐剧项目需要依靠政府资助、文化基金扶持,所以在音乐剧的艺术性上做的不错,但很久没有出现商业制作。以我自己的经验,上一个大型商业项目可能还是《雪狼湖》。那么现在我们做出的《大状王》,除了艺术上的追求之外,接下来也要再想一想,如何去拓展市场。要知道《雪狼湖》能够成为这么风靡的作品,公众明星的参与也是重要因素。那么《大状王》今后能否依靠自身成为戏剧品牌吸引更多人为它走近剧场,这是一个考验。
岑伟宗:我个人更希望说是在《大状王》之后,先有更多“读剧(剧本围读)”出现。因为音乐剧是一个综合的艺术,它要从一个创意慢慢发展出一台戏,那么“读剧”就是基石。而且“读剧”所需的支持经费并不高,比起一上来就目标要做一个大戏的成本低很多。但这却给予这个剧本更多接受检验的机会。通过其他人给出的意见来进行不断的修改提高。如果未来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音乐剧行业,那么我希望多一点人从开始“读剧”这件事做起。
文汇报:最后代替更多内地想看《大状王》的观众,何时能来内地演出?听说最大的困难在装台週期长?
方俊杰:确实目前我们的舞台看起来没有什么复杂,但看了剧的朋友就会知道,涉及的舞台装置和设计并不少,确实要花很长时间去搭建。可能有些人会建议做一个巡演版,简化舞美;又或者说是你先开档期吧,确定好了再慢慢调。可我认为这对看所谓“简化版”的观众不太公平,因为明明有完整的版本可以带给大家更好的体验,为什么只能看到简化版。不管最终能否成行,我们希望给每一位观众最好最完整的体验。
图:香港话剧团供图,摄影Thomson 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