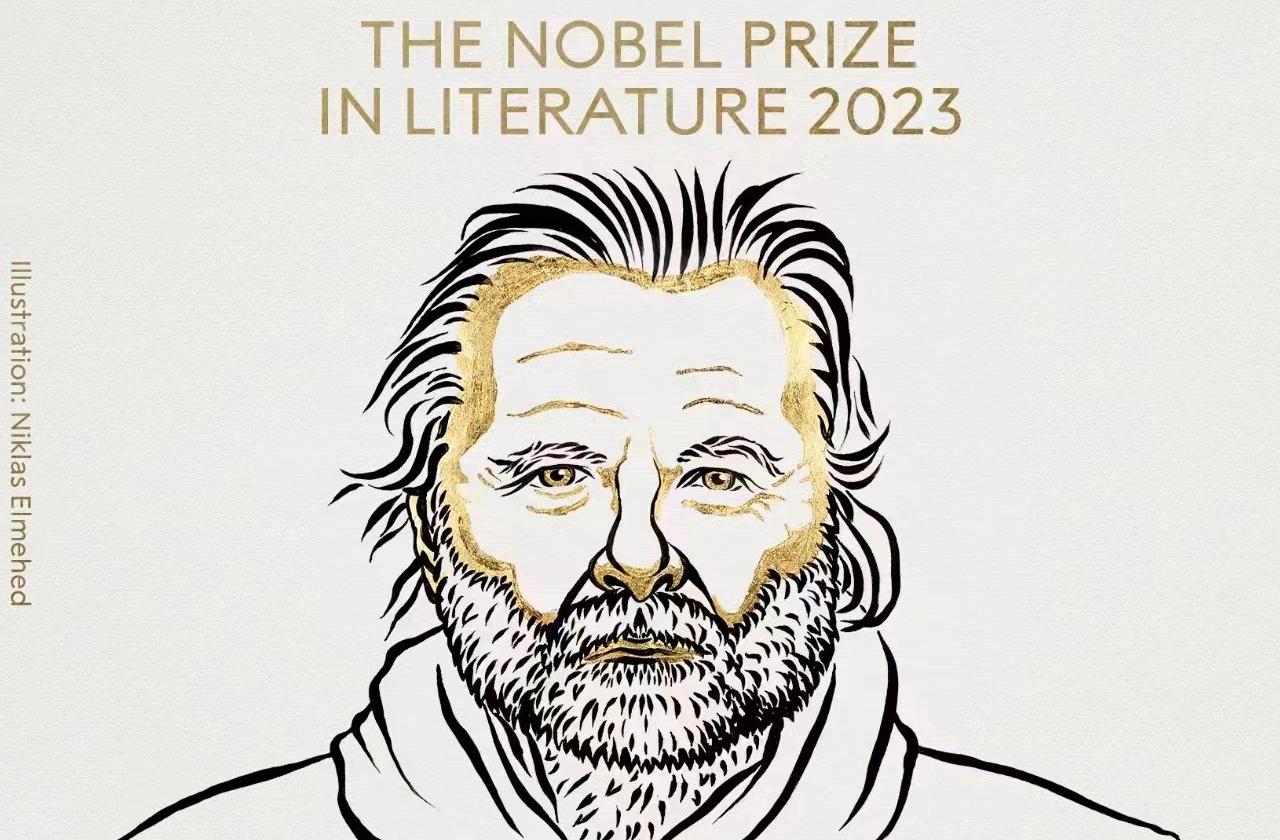简洁:我要写一部小说,并且非这样写不可
1.
我是一个经常陷入写作黑洞的人。对于一个想要以写作为生的人,这点很致命。
这大概是《数千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写了这么久的原因,因为在它刚生长出来的时候,没有像我熟悉的杂志一样deadline的概念。它是混沌的,自由的,没有边际的。
写下这部书第一行字时,是2019年,我32岁。
“我要写一部小说,并且非这样写不可。”
这个感觉,在当时非常强烈。
即使在这篇小说还不到两万字的时候,即使在它长时间停滞的时候,它的存在本身,对我而言,就是一件找到写作归属感的事。
这部小说写了三年多。但事实上,准确的时间线是,前面不到两万字写了两年半,后面的八个月写了四十二万字。
就像威廉·福克纳所说的:一个不愿动的人,一旦动起来,就会持之以恒动下去,就跟他坚持待着不动时一样,好像他不喜欢的倒不是动本身,而是开始和停止。我觉得我的懒惰,一直都是这样的。
在这四十多万字的过程中,读者的留言每每让我感动,我以为受众很窄的这篇小说,收到了很多的共感。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想清楚了我要写的是什么。
我想要以80后、90后这一代独生女的视角,记录我们好像十分幸运,但在长大之后明白过来,其实还是在和生活斗争的成长故事。以成年后的视角,去审视童年和少女时期经历的一些事,真相其实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完成对童年和青春时期的一种治愈。
 《数千个像我这样的女孩》
《数千个像我这样的女孩》
这个治愈,我完成得既坚定、又懵懂。那时看到梁永安老师的一句话:“真正的治愈不是说人没有痛苦了,而是面对自己的痛苦从何而来,能够驾驭自己的痛苦了。”我当时觉得,我的写作,可能就是在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2.
这本书的一个内核,是我反复提及的村上春树的一句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知都胜于无知。不管带来多么剧烈的痛苦,都必须知道那个。人只有通过知道才能坚强起来。”
这不仅是我写作的态度,也是我做人的态度。在后来写《废刊少女》的过程中,我明白过来,这可能不是我一本书的内核,而是我所有书写冲动的内核。
在书写中,我沉浸到时空和记忆中,去探寻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的“知道”。有很多读者留言说,当时没有想明白的一些事,在看到张小莫的经历时,突然明白了。在明白的同时,完成了这场治愈。于我自己,其实也是一样的。
反馈的读者,不仅是80后和90后,甚至还有00后,他们留言说虽然年代不同,但感觉我写的就是他们的故事。这让我意识到,我写的可能不是一个独属于我的故事,而是一个代表了更大多数人的故事。甚至有时,我是从他们反馈中才意识到的真相的另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我的超越了当时所要完成的初心。
有喜爱这本书的朋友,统计说我在这本书里写了五十余位不同年龄的女性,而她们拥有不同性格与成长经历,然后给我一个一个地数他印象深刻的人物。说这些女性的存在,构成了整个张小莫宇宙。听到这个数字,我愣了一下,我并没有把这本书当成群像在写,但最后的呈现,是超乎我想象的。
3.
写完这本小说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失落的感觉,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深。
不舍的感觉最重的时候,是写最后几章的时候,心里知道它将要结束,这段漫长的旅程终于要走完。我和很多朋友一样,希望这本书写得长长久久,把张小莫的人生再看得长久一些。因为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很容易感到幸福,那是一种在重来一遍的成长中,被疗愈的细水长流。但作为作者,我又比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它要在这里结束的理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这样一件事而感到幸运:我任性地写了这样一本书,并且有人愿意看。起初,我并不知道它的读者在哪里,但我知道对于这个故事,我非写不可,而且非这样写不可。
大概写到三万字的时候,就与出版方接触,所以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已经预想了这本书到纸质书时会有怎样的呈现。写到二十五万字时,我最大的焦虑是它的字数会太多,一本书也许出不完。在那时我和编辑朋友们商量,他们让我放心大胆地写,不要用字数来限制自己的创作。
这个不用限制字数的可能性,让我一下放松下来,获得了写作最大的舒适度。在我写作的时候,仿佛一只透明的水母,沉入辽阔斑斓的记忆之海,全身心地去感知着透过身体的景象,那些映照在我身体中的景象,我试图事无巨细、纤毫毕现地把有意义的部分全部摄取出来,然后放在这个故事里。
在每一个书写的夜晚,我都在做着这个沉入海底去取材的旅程。这是一片让我非常舒适的海域,可以说,从我的第一本书《少女与霓裳》开始,少女时代就是让我有书写欲望的一片海域。
为什么会这样,一开始我以为,这是因为这个时期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后来我发现,并不止这样,这一时期的内涵要更复杂而深远。以至于,我是这样怀念它,想要书写它,但又好像没有好好地面对过它。
我模糊地意识到,这份书写可能是独特的。
那种感觉,就像重新过一遍童年和少年,仔细检查每一份伤痛与隐刺,观察它们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有这样一句话:有人用童年治愈一生,有人用一生去治愈童年。但我在书写的时候,觉得童年和一生的关系可能并不这样对立简单,它们有相互疗愈的可能性。
在我重新一口气读完这四十六万字时,我仍然会为张小莫那种小兽般敏锐而清醒的观察而折服。那种细致入微的观察、体会和惊人的感悟,并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在我像水母一样沉入海域时,极致地张开五感,通过张小莫的视角重新经历一遍事件时,属于她的观察和感悟。
少女张小莫,比我敏锐、比我聪慧、比我坚韧,透过她的身体,我可以不惧进行任何记忆的感知和读取。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有了超脱记忆本身,进行更自由的创作和书写的可能。
4.
全书最开始,我从童年关于记忆的一个创伤开始写起。
事件微小,但后遗症很绵长。至今我回忆这件事时,都带有晕车一般的眩晕感。成年之后的我,仍然非常害怕找东西,因为试图回忆这个动作,就可以引发我的痛苦。但通过张小莫的眼睛,我沉静下来,再次经历这件事时,我奇异地感到了一种治愈感。当她完完整整地分析出事情的全貌,直面事件的时候,会有点像日剧《SPEC》里户田惠梨香在寻打破案灵感时,把关键信息都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然后撕碎往空中一撒,碎片像雪花一样慢镜头掉落的瞬间,突然窥到了某种真相、被闪电击中的感觉。
原来如此。
这种感觉,出乎意料地让人感到疗愈。
并不是那些伤痛都不存在了,更像是手指嵌入了一根毛刺,要把它挑出来也许会剖开更大的伤口,留下更大的疤痕,但把它清理出来的内心的舒爽感。还有可能是,这根毛刺挑不出来,但光是知道那隐隐的疼痛是毛刺造成的,而不是像别人说的根本没有刺,是自己太敏感的心理作用——光是知道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让人安定下来。
我渐渐地对这种感觉上瘾,在书写中不断地重复着整理、撕碎、洒落、重组的这个过程。书中张小莫对小学班主任玩弄人心的领悟,对孤立轮回的解读,对男孩规则的发现,对同桌的观察,对如何度过被孤立的时间的了悟,那些让读者觉得惊艳的恍然大悟 ,都是在这种书写过程中完成的。
重看一遍的时候,我甚至想对这些领悟做笔记,因为感觉不仅对经历这一切的小少女有用,对已经成人的我也依然有用。更让我踏实的是,不只是87年的读者,90后乃至00后的读者,都在留言中说,虽然时代不同,但我写的仿佛就是他们经历过的童年。
大概是因为这样,我对这段书写的过程,一直很珍惜。在水母一般巡视记忆之海时,我恨不得一寸一寸地挪过,甚至有一些不给自己之后的写作留余地的意味。我以一种毫无保留的姿态进行了书写,所有的灵感、意象、感触,还有发散出来的想法,在每次书写时,我都要默念一遍眼耳鼻舌身的顺序,不放过沉浸到记忆中的一点细节,季节,天气,风物,甚至空气的湿度。生怕我错过了一点,就会错过撕碎纸片时撒落时的灵感。
5.
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故事是可以与现实进行一比一的刻板还原的。
我在采访邓一光老师时,他这样说过:“要完成故事的叙述,必须建立一个包括写作者的我和阐释者的读者都能够确认和确信的叙事机制,仅仅依靠虚构,让故事建立在一段完全不真实的历史上,我的写作一个字的意义都没有。 ”
他这样和我解释真实背景与虚构故事之间的关系:重建真实的背景,于故事的成立非常重要,在结构性地还原了历史真实的基础上,才能开始属于审美的文学叙事:遣构语言、编织情节、塑造人物。
在这一本书的写作中,我深刻领悟了这一点。从结果来看,完成得还不错。我找到并建立了这样一个叙事机制,并且在此之上,建立了我的文学叙事。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其实只要看这是否是一个好看的故事就足够了,但要和身边的人解释什么是文学叙事,就会有些困难。只有当他们发现,寻找原型的工作,不仅是徒劳的,而且是让人迷惑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我写的是一个故事,而不是还原回忆。我也并不希望别人以这样的心态来读这个故事,因为这对于我想书写的内涵而言,是一种本末倒置。
讲一个温暖又好笑的事,故事里的尹松,原型里有一部分是我高三的同桌,但她并没有染过蓝头发。在看小说的时候,一直并不确定那个人是她,但当她确认了一个细节后,说花了两天的时间去想自己有没有染过蓝头发,难道是那时太叛逆了,连自己都不记得了。
她和我讲了这件事后,我们俩都笑个不止。我也从她的反馈中,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叙事下,真实的错觉。那些被我撕碎之后重建的叙事,也许正因为这样,与更多的人的童年和少年有了贴合度,无论在天南海北,无论是在80年代末还是00年代出生的朋友,都觉得和张小莫重新走过了一遭少年时代,所以触动,所以不舍的缘故吧。
没有人会比我更不舍得结束张小莫的故事,但就像前面说的,理由有很多,我也解释过几次。从叙事上讲,时间再往下,就要建立一个新的地图,在全新的世界里,人物和逻辑都要重建,看到已有人物交集的可能性很少。从立意上,我希望将时间线划在高考之前,这个也许是人生中最后一次的相对公平的时间点。
但最重要的理由,是我对张小莫的珍惜。
在她尽了自己所有努力之后,值得读者去想象一个更广阔的未来。
最后,我想记录一下,和给这部书封面授权的画家赵绮莉的渊缘。
2019年我在豆阅开始这篇小说写作时,故事还没写,就先把豆阅的封面图定好了。
授权给我用图的是一位画的主角总是爱丽丝的画家赵绮莉。她笔下的爱丽丝,穿越过故事中的种种幻境,有悲伤的,孤独的,无措的,倔强的,我之前很喜欢一幅头嵌在玫瑰花里,像戴着小红帽一样的爱丽丝,画家大方地应允我,之后可以把她的画给我用在书封和插图。
所以,还未开笔,我便想到了那个眼神让我难忘的女孩,再次找到她授权。在开篇,那千百种爱丽丝我选了一个即将掉入激流中的爱丽丝,如我的朋友所言:女孩掉入庞大的世界,这个意象多么贴切。
在小说正式开始写作后,我和绮莉在深圳见了一面,除了封面授权之外,她同意我在正文中用她的画作来做插图。所以在豆阅的电子版里,我用了五十张她的画作放在章头,每一张画作的寓意都有契合的部分,让我在初期写作时也得到了一部分灵感。
因为这样的羁绊,所以纸书出版时,编辑也同意继续选用绮莉的画作为封面,也是我很喜欢的两幅画。最后出来的效果确实十分惊艳。
新书拿到手上时,上下两册,沉甸甸的。有一种人生就此有了底色的感觉。这是我第一部长篇小说,我写它的时候,就像写自己最后一本书一样,毫无保留。而如今,在它之后我又写完了两本长篇小说,再回头看时,依然有尘埃落定之感。
大腰封的设定,上下册的封面,内文的纯质纸,每一个部分我都满意。人生的某个部分,在这里存档。而当时一起陪我写完这部书朋友,以及最新翻开这本书的朋友,也希望你们阅读愉快。
最后的最后,感谢陈丹燕、路内和陈楸帆三位老师的挂名推荐。我的三本书都请路内老师进行了推荐,可以说他是在我写作上见证我成长的一位作家,我和他在这部书最开始写作时的长谈,对这篇小说的创作有很大的意义。
陈楸帆老师我采访过他五次,彼此已经非常熟悉,但说起来,是我更熟悉作为作家的他。这次请他挂名推荐,请编辑寄了全稿六百多页的样稿给他,刚收到时他吓了一跳,最后他全翻完了,说很容易看进去,和我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作家。我想,这大概是这部小说可以成为我写作道路上一个锚点的原因。
陪我重走了一段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小莫,如我最开始选的那幅画的寓意一般,像女孩掉入庞大的世界,而在小说读完的时刻,我们终将找到着陆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