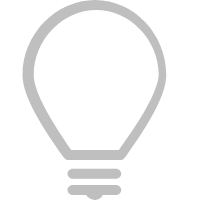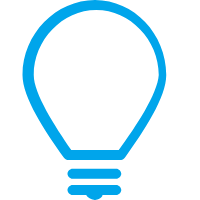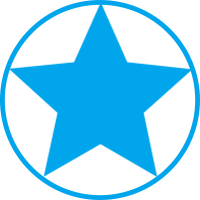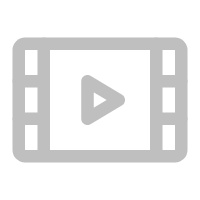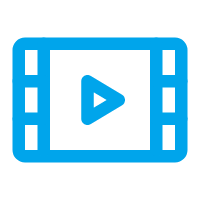守候微光采访了9位在武汉参与过一线疫情报道的摄影(视觉)记者。他们供职的媒体有通讯社、党报、都市报、英文媒体;有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也有外地人;有刚工作的见习记者,也有十几年始终冲在一线的“老手”。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分享了在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业务经验和个人思考。
这是系列访谈的下篇。

6、疫情下,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不愿被拍摄,相机有侵犯性和曝光性,这种时候你如何调和报道任务与采访对象的感受?
史阳琨:最近我和一位日本的摄影师朋友小原一真也讨论到这个问题,他在拍摄二战受害者时面临着这样的“权限困难”,不知是不是与创伤心理有关,与我在武汉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我看到《纽约时报》做的一些疫情相关的视觉报道,病人家属给的权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这可能跟文化差异也有关。我的原则还是首先尊重采访对象,努力跟病人和家属做沟通,比如能不能实名、能不能出现正面或者侧面的肖像。不理想的状况就是使用化名和马赛克吧,这也是新闻摄影经常要面对的伦理矛盾。

4月8日,武汉,上班路上的地铁工作人员。史阳琨/摄
鲁冲:像苏珊·桑塔格说的,拍照本身就是一次“拥有更霸道的权力的事件,干预、入侵或忽略正在发生的无论任何事情”。被拒绝的背后有很多原因,有的是担心家人因此受歧视,有的是不想正在上网课的学生们知道自己在方舱医院……所以更多的时候是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如果镜头面前是我的亲人我会怎么做。
钟锐钧:我拍摄的题目还好。医护人员由于和我很熟悉,所以都很配合。后面武汉“解封”前后我也经常扫街,武汉人其实很开朗,我在拍摄中遇到的阻碍其实并不大,大家都还蛮愿意被拍的。我觉得摄影记者脸皮厚一点还是有用的,还有就是沟通能力很重要。
陈卓:患者很怕自己的隐私泄露。我明显感受到一些患者受到歧视了,有几个患者都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了,他们的邻居亲戚也不愿意跟他们来往。我的很多拍摄对象都是从ICU病房或隔离区一路跟拍下来的,他们都比较信任我。实在不想接受采访的也不勉强,我就跟对方说我们还是朋友,等这个事情过去了我们再继续沟通下一步的信息。拍摄的时候都跟拍摄对象现场沟通过,确认没问题才发表。不过也遇到过那种发表之后对方反悔的情况。
和采访对象做朋友,这一点很重要。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为对方着想,而不是为了采访而采访。我们所做的不是一份冰冷的工作,越是大的事件之下,越要让你的职业作为有暖人的温度。

2月16日晚10点,金银潭医院内,涂盛锦和曹珊夫妇在车上睡下。他们都是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因为家离医院较远,救治患者又走不开,他们在疫情期间选择住在车中。夫妻俩都参加过2003年武汉抗击“非典”的工作。陈卓/摄
沈伯韩:陌生的摄影者和被摄者,大多会处于一种相互“博弈”的“紧张”关系中,无论是在疫情下,还是平时。有时候通过与被摄者聊天或者一同做点什么事情,能慢慢消弭掉这种“紧张”与“对立”,会让被摄者放松下来,然后再举起相机,就会相对比较容易。但这也可能会错过一些好的动作瞬间、人物表情和情绪等。所以这个度和时间点的拿捏就很重要,没有定式和规律能去遵循。但最核心的一点,是尊重以及同理心,必须要把被摄者当成一个人去真正地尊重,去聆听ta的声音和需求,这样才不至于出问题。我在武汉街头拍摄,也遇到过与被摄者有点小争执的情况,后来以我尊重对方要求删除照片结束,双方都能理解和尊重对方,这样就可以了。
7、在此次报道中,除了常规的静态照片,你是否还使用了视频、航拍等其他视觉表达方式?
沈伯韩:我会在报道中使用无人机拍摄。无人机能提供一个额外的、有些不同的角度和视觉效果,有时候会有好的照片产生。武汉“解封”那天,我用无人机拍摄了一张车辆排队通过武汉西高速收费站的照片,如果没有高空的角度,那长长的车流是无法表现出来的。记得拍这张照片时,我心中还是蛮感慨的:“封城”这么久,普通人终于可以开车离开武汉了!

4月8日凌晨,车辆排队通过武汉西高速收费站。当日零时起,武汉市正式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有序恢复对外交通。(无人机照片)沈伯韩/摄
李隽辉:这次在武汉视频拍摄的是比较多的。可能是我介入时机较晚的原因,在看了疫情初期相对“简单粗暴”的视觉信息后,我感觉需要更精细且耐咀嚼的视觉报道,在那个阶段,视频从信息表达和叙事的完整性上都比静态图像更好一些。3月中旬的时候,我和同事李峥苨拍了一个关于康复驿站的视频,那些满怀着希望从医院走出来的患者在康复驿站中复阳的复杂焦虑情绪,用图片和文字是很难言说的。但是视频因为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发出来,也是一个遗憾。

2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血液净化中心的护士们在等待即将送到的援助物资。这支由20多名专科护理人员组成的“护肾小队”,负责为重症及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做血液净化,清除体内细胞因子风暴。李隽辉/摄
陈卓:现在图片的传播太平面化了,没有感同身受的感觉。视频有声音和流动的影像,能够更直观地打动你,所以疫情到后来我基本很少拍照了,一直用视频在记录。把视频该记录的记录了,再去给现场补一些肖像,其实很快。在实际使用中,高清的视频截图放在报纸和新媒体也是足够用的。
现在工作中我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拍视频,如果以后转型要求这样,那没办法。照片和视频其实有点冲突,拍视频的时候就把决定性瞬间丢了,拍照片的时候记录的连贯性又被打乱。有时候我们也很头疼。如果真的要选择职业的话,还是术业有专攻吧。
钟锐钧:没有,照片都还没拍好呢。
赵迪:其实无论是图片还是视频都是在用视觉的方式呈现,但它们也有各自的语言特点和生产逻辑,我会根据不同的内容来进行选择。
8、这次疫情报道中,很多媒体使用摄影记者的照片制作海报等视觉产品来推广。你是怎么看待这种现象的?在拍摄中,是否会有意识地寻找更易传播的画面?
史阳琨:我觉得这种方式在新闻摄影面临困难的今天是好事吧,照片本身得到了更大的传播,对文章的导流也是明显的。我为Sixth Tone拍摄的武汉解封的系列海报传播后,我自嘲从一名“新闻摄影师”成功转型为“海报摄影师”,我想要自己警觉的是这两个东西是有挺大差别的。
但我在拍摄的时候不会想这些,作为一个报道摄影师,就是去拍到好的照片,海报等视觉产品是后方编辑和设计人员的工作。

史阳琨为澎湃新闻Sixth Tone拍摄的照片被制作成海报。
沈伯韩:海报是蛮好的一种对图片的应用,算是此次疫情报道中照片传播的一个特色。但海报对于照片有一定的适用性要求,比如最好是竖片、背景尽量干净、画面主体的结像尽量大、如果画面能有一些额外的意韵会更好……我在拍摄中,还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能拍到这样的画面那当然好,在时间、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有意识地去寻找,但拍不到也不会强求。
陈卓:海报利于传播,更深入人心、更直观。它不像看一个图片故事需要那阅读那么多文字和图,信息量太大,很累。我拍了很多利于传播的照片,专门做过一批医护人员的海报。拍摄海报照片和其他拍摄任务没有冲突,快速拍完就去拍别的工作了。
9、此次报道中,你都用了哪些器材?在不同的场合拍摄时,如何选择器材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史阳琨:报道过程从头到尾就使用了一台富士的中画幅数码GFX-50R,一支32-64mm/F4的镜头,我的想法就是没有非拍不可的画面,所以没带定焦、长焦和闪光灯。这台相机也是专门去找朋友借的,就是为了更好的画质。
赵迪:主力是一台佳能5D4相机。我首先会对场景进行预判,如果距离可以很近的话,就带一支24-70mm镜头或者广角定焦镜头。如果无法近身拍摄,则会带上70-200mm镜头。很多时候也会用到手机,因为手机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拍摄,比较轻便。

2月19日,武汉市百步亭社区,窗台边的一位老人。当天是武汉市为期3天的集中拉网式大排查的最后一天。赵迪/摄
钟锐钧:我带了佳能RP和1Ds3,微单用于病房,单反用来拍肖像。这次带的器材都是比较轻便、比较适合拍新闻事件的配置,然而我跟同事在后期扫街拍人像的时候有点后悔没带中画幅的机器,那样拍人物的透视感会更好。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拍到后来才会比较清晰的知道想要做一组什么样的东西。
李峥苨:相机机身是佳能5D3、6D,镜头包括24-70mm、70-200mm,35mm。后期在同事李隽辉的帮助下尝试着用无人机拍摄到了意外的素材,所以有点后悔没有更多地使用无人机。

2月21日,武汉火神山医院感染八科,一名医护人员准备穿上防护服进入病区。为了防止污染,防护服不能着地,穿着过程中需时刻注意。李峥苨/摄
赖鑫琳:考虑到器材消毒的问题,我就带了我认为最可靠的佳能1DX和1DX2,两台机身,一台挂广角,一台挂长焦。尤其是在病区内采访,我广角通常会选择35mm定焦,长焦的话用70-200mm,有时候挂50mm定焦。病区内不能换镜头,两台机身可以满足很多的拍摄需求。佳能的机身在消毒的过程中整体表现还是很可靠的,有小Bug但是我两台机身最终还是处于工作的状态。
沈伯韩:我会根据自己的采访内容来选择所使用的器材。如果是采访普通新闻,为了更快地做出反应拍下画面,我会携带佳能 1DX2、5D3机身配24-70mm/f2.8(或16-35mm/f2.8)和70-200mm/f2.8镜头。如果是在街头拍摄,我会用 35mm/f1.4或徕卡ME机身配35mm/f2镜头,以免太过引人注意。如果是去医院采访,因为空间比较狭窄,而且室内光线一般不好,我会用两个佳能机身分别配24mm/f1.4和70-200mm/f2.8镜头。有时也会用50mm/f1.2镜头。
陈卓:机器是佳能5D4,16-35mm,70-200mm,24-105mm,50mm定焦4个镜头。医院里主要用24-105mm,一镜到底。在街上就随便用了。
10、结束报道后,你是如何整理和编辑自己照片的?
沈伯韩:在武汉68天,我拍摄的照片加视频总容量大概2.2TB左右。每天拍摄的照片我都会单独建立一个以日期和地点为主要标识的文件夹,并同时在A、B两块移动硬盘上备份。如果一天去很多个地方,会每个地方都单独建立一个文件夹,以防时间久了会记错。在拍摄的时候,到达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先用手机拍一张大场景的照片,因为手机照片带有时间和地点信息,这样在整理照片时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参照作用。
我把经过挑选和处理的照片大致分为三个类别:战疫(医务人员、病患),抗疫(社区工作者、保安、志愿者、其他工作人员等),百姓生活,然后根据使用目的不同组合编辑这些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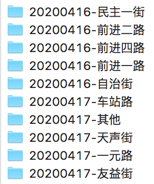
沈伯韩将4月16日和17日所拍摄的照片根据时间、地点不同分不同文件夹来存放。
史阳琨:本来我是有计划要独立做一个图片故事的选题,但是因为时间和任务种种原因没有完成。回到上海之后我就开始整理这17天里拍摄的所有照片,发现可以让图片自己去讲一些故事:在武汉解封前后两周的时间,新冠肺炎患者、医生、普通人……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状态里面。所以我就将它们编辑成了一个独立的图片故事。
彩色照片放在一起会显得杂乱无章,所以我决定把它们都转成黑白。在文字方面,我是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去写的,这个也是我跟我们编辑讨论的结果,通过这种类似记者手记或者是个人感受的文字,把读者带进我的图片故事里面,营造一种感受和情绪,而不是去呈现某个具体的事件。
11、密集的疫情报道是否对您的心理及身体健康造成了影响?结束报道后,您如何调整自己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赖鑫琳:心理压力比较大吧,在武汉期间工作节奏很快,情绪上的波动也比较大,导致了睡眠不好,回来之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虚幻和不真实的感觉,走在街头有时候突然间就觉得自己还是身在武汉,晚上也会梦到自己穿着防护服在拍摄。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调整吧,渐渐地都会好起来的。
钟锐钧:我的睡眠受到了一些影响,回来后不太想工作,休息了不短的时间。我觉得要完全让自己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应该不可能吧,毕竟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变故。活着真的很幸福,要珍惜当下。

3⽉29⽇傍晚,武汉市武昌区汉街,一名园丁在为第⼆天汉街重新开业做准备。钟锐钧/摄
沈伯韩:在武汉工作期间,一直比较焦虑。一方面觉得要抓紧时间多拍一些照片;另一方面,对于一些事件和人物线索也掌握得不够,很希望自己拓展拍摄的广度和深度,能拍到好照片。身体方面压力也比较大,腰伤复发也只能贴贴膏药忍着。
回北京后,在哪里洗手都会遵循7步洗手法;在外拍照的间隙,也会不自觉地拿出酒精把自己的手喷一喷……这些在武汉养成的卫生和生活习惯,恐怕会延续蛮久,也算是武汉之行给我留下的有益遗产吧。
陈卓:有段时间比较“丧”,有时候做梦还在ICU里和医生一起抢救病人,听到病房里那种“嘟——嘟——”监护仪的声音,睡不好觉。过了一阵子慢慢就好了。
12、这次报道有没有什么遗憾?
史阳琨:在常规工作报道外,我没能完成个人专题。因为每天的时间都被打碎了,还要完成文字稿件的配合工作,导致后来没有精力去完成一个有深度的专题,有一点遗憾吧。
赖鑫琳:漏进一次红区,错过一场采访,漏掉一个瞬间,拍虚一张照片……在疫区采访,遗憾每天甚至每时都在发生。
最为遗憾的还是那张走红网络的上海医生带老人做CT看夕阳的照片。我曾经离那张照片特别近,画面中陪老人看夕阳的刘凯医生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医生,我是跟随这支医疗队一同进入的武汉,与医疗队员们同吃同住,他们支援的医院也就是那张照片的拍摄地,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也是我在武汉期间去的最频繁的医院,可是我错过了。
陈卓:1月24号晚上路过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里面就诊患者很多,我只戴了一个医用外科口罩,没敢进去。那天下雨,还看到一个人撑着伞坐路边打吊瓶,很心酸,也有一点恐慌,觉得能离远一点就远一点。那个照片很遗憾没拍到。当时也不知道病毒的作用结果是什么,“小米加步枪”进医院的话感染几率很大。过了一段时间戒心才放松一点,才敢放开手脚去采访。不能说“不怕死”,到我们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要考虑的因素还是很多。

2月16日,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雪后初晴,一名行人张开双臂享受阳光。鲁冲/摄
李隽辉:其实工作里没啥遗憾的事情,都慢慢会“和解”。“遗憾”的还是工作之外,即便现在身在北京家中,回想起几个月前遇到的患者和医务人员,还是会有人生无常的感觉。为每一个遇见的不幸感到遗憾吧。
曲俊燕、孔斯琪 |采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