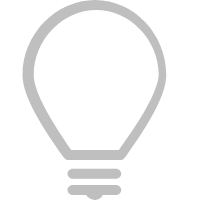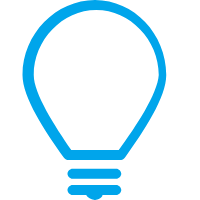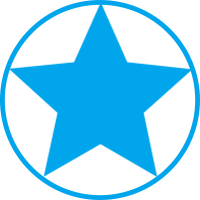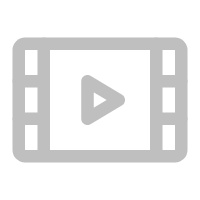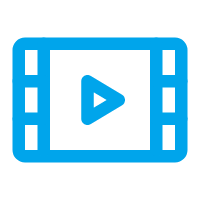接到报道疫情的通知时,22岁的年轻记者鲁冲刚从北京回到老家武汉半天。他回家只为了一碗热干面,却不曾想到,在家乡一待就是108天;武汉长江日报的摄影记者陈卓,在“封城”前一晚刚把老人孩子送回老家,接到报社通知后,又说服妻子一起急忙往回赶;还有更多的外地摄影记者主动请缨,心想“终于轮到我了”,有些激动,也有些忐忑。
几个月的疫情中,摄影记者和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志愿者们一样,是“逆行”的人。他们用镜头记录了历史、收获了经验,也留下了遗憾。
守候微光采访了9位在武汉参与过一线疫情报道的摄影(视觉)记者。他们供职的媒体有通讯社、党报、都市报、英文媒体;有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也有外地人;有刚工作的见习记者,也有十几年始终冲在一线的“老手”。他们以不同的视角,分享了在公共突发事件报道中的业务经验和个人思考。

1.去武汉之前,你是否有拍摄计划?在武汉实际的工作内容和节奏是怎样的?
赖鑫琳:没来得及做很详细的拍摄计划,但基本方向还是有的。我的报道任务很大一部分是围绕上海援鄂医疗队,但我知道不能把自己“框死”在这里,还是要关注整个武汉的疫情。
在武汉整体的工作节奏都是很紧张的,几乎把每一天都当成是在武汉待的最后一天。
沈伯韩:谈不上比较系统和具体的拍摄计划。因为通讯社的工作性质使然,我报道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而且去之前我也不想形成太多先入为主的观念。
在武汉工作时,如果有一些硬新闻,就会与同事合作分摊去完成。除此之外,就是自己联系医院、社区等采访,或者去街头拍摄。工作最紧张的一次是拍摄武汉重启,4月7日下午2点左右出门拍摄,一直到8日晚上10点左右发完稿,大概睡了3个小时。
 2月17日,武汉,上海援鄂120急救车司机侯敏杰驾驶着车辆疾驰在夜色中。赖鑫琳/摄
2月17日,武汉,上海援鄂120急救车司机侯敏杰驾驶着车辆疾驰在夜色中。赖鑫琳/摄
鲁冲:没有计划,就是想去现场。这次我的工作内容和以往有很大不一样,在武汉文字、图片、视频3种形式(的报道)都有去做。我自己也比较“贪婪”,每次去现场都希望尽可能捕获更多的素材和信息。
而且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我们在报道之外还会穿插一些别的“工作”,尤其是在疫情早期,防疫物资比较匮乏,大家需要想办法找到物资然后进行合理分配。
钟锐钧:开始没什么计划,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带闪光灯和柔光箱拍肖像,因为我平时拍摄人物也是这个配置,我觉得能在日常拍摄之外有多一种可能性。在武汉,我每天都往返在医院和医疗队所住的酒店之间,肖像拍摄之余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我都争取能够多进几次病房,因为汉口医院是这次武汉疫情的最核心区域之一。
 4月4日傍晚,武汉汉阳江滩公园,散步的市民。钟锐钧/摄
4月4日傍晚,武汉汉阳江滩公园,散步的市民。钟锐钧/摄
陈卓:没有特别的计划,我主要想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出发,去关注这个大背景中人的命运。
现在都是滚动式的融媒体发稿,摄影记者基本上单兵作战,有文字记者就配合文字。我们是武汉本地媒体,借助武汉市各医院和政府通讯员的力量发掘了很多好的线索,去了之后再自己采、自己拍,策划选题的走向。报道节奏上,每天的机动性很强。我们都有车,办了防疫指挥部的通行证,交通上方便很多。
 2月17日上午,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隔离病区,44岁的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医师涂盛锦(左)在办公室和同事沟通工作。陈卓/摄
2月17日上午,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隔离病区,44岁的重症隔离病区副主任医师涂盛锦(左)在办公室和同事沟通工作。陈卓/摄
史阳琨:从接到通知到出发中间有两三天,我跑去找朋友借了一台中画幅的数码相机,因为我觉得如果带单位的5D3画质上的损失是可惜的。
武汉很大,因为“封城”交通不便,我每天开车带文字同事去各地采访,主要是给特稿拍摄配图,我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好视觉配合,在文字推进采访的基础上,争取更多摄影表达的可能。
2.谈谈你在武汉拍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张/组照片吧。
赖鑫琳:3月9日晚,我前往位于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记录休舱前的最后一夜。当晚,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江文洋医生最后一次在武昌方舱医院值夜班。看着空荡荡的床位,他躺倒在空病床上休息了片刻。
 3月9日晚,武汉市武昌方舱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江文洋医生结束了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班后,躺在空床上,如释重负。赖鑫琳/摄
3月9日晚,武汉市武昌方舱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江文洋医生结束了在这里的最后一个夜班后,躺在空床上,如释重负。赖鑫琳/摄
那个画面简直太“魔幻”了,穿着防护服的他像极了一个宇航员,在太空中执行了漫长又艰难的任务之后,终于落地。我拉了一把椅子站了上去,把这一幕拍了下来。看到我拍摄,他赶忙起身,收拾了一下,走出了污染区。后来这张照片火了,在各个平台的阅读量累计超过了3亿,也成为整个武汉方舱医院报道中比较有标志性的一张。
钟锐钧:我从2月11日开始就和广东医疗队住在一起,跟他们进入过两次病区,和一些医务人员很熟悉,在这个前提下,我决定开展我的个人选题:拍一组出病房时脱下口罩的医务人员肖像。我希望用拍摄人物一贯的方式给他们拍摄一组充满脸部细节的照片。



 《最美逆行者》钟锐钧/摄
《最美逆行者》钟锐钧/摄
这组照片传播的比较广,也收到了不同的反馈。其实(疫情)这么大一个事情,每个记者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拍摄,我觉得至少这对每个医护人员来说是有意义的,能在疫情中有一张比较正式的照片,这也比较契合我最早的出发点——为医护人员做点什么。
后来我们想围绕武汉”解封“做一个图集,在扫街的过程中发现,虽然大家还是戴着口罩和各种防护,但有些人会穿着很特别的衣服出门,尤其是中年人,很多都是疫情以来第一次上街,所以可能需要有点仪式感。后来湃客工坊转载的时候对这组照片做了更细致的编辑,把每个人身上的时尚元素提炼了出来。
 4月5日,武汉汉口天声街,60岁的许叔叔近3个月来首次出街,为此特意搭配一番,除了一身笔挺西装,他还有一张讲究的手帕。钟锐钧/摄
4月5日,武汉汉口天声街,60岁的许叔叔近3个月来首次出街,为此特意搭配一番,除了一身笔挺西装,他还有一张讲究的手帕。钟锐钧/摄
沈伯韩:在常规采访之外,我花了不少时间在武汉老城区游走。那时,武汉街头最有特点的就是各式各样的围挡,红黄蓝绿很多种颜色。无论在物理和心理层面,这些围挡都分隔出了两个世界——围挡外是“自在、自由、方便”的生活,围挡内则相反。在这些围挡旁能看到一些武汉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恐怕是很难再有机会重现的一种社会场景。这组照片姑且取名为《DANG》吧。
 4月17日,武汉市一元路,开川菜馆的一家人透过店铺前围挡上打开的孔洞向外张望。沈伯韩/摄
4月17日,武汉市一元路,开川菜馆的一家人透过店铺前围挡上打开的孔洞向外张望。沈伯韩/摄
 4月19日,武汉市前进一路附近,围挡里的居民。沈伯韩/摄
4月19日,武汉市前进一路附近,围挡里的居民。沈伯韩/摄
陈卓:拍了很多人物故事。其中有一个志愿者车队,他们本来是给医院送物资,听说救护车全都在送新冠病人,孕产妇没有车,于是自发组织了一个待产孕妇用车群,跟医护人员和其他志愿者对接。车队5个人几乎24小时在线,他们在武汉不同的区,都一对一地跟待产孕妇对接好,每个孕妇的产期都有排期。当时其中一个志愿者跟我说,在疫情下,每天听到的都是不太好的消息,但是我把这些产妇送到医院,看到一个个新生命诞生,就是给这个城市以希望。
 2月22日18时10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妇魏利静顺利生产,助产士把孩子递到她面前。魏利静由一支名为“W大武汉紧急救援队”的志愿者车队送至医院,该车队5名成员专门接送缺乏交通工具的待产孕妇,成为“新生命的摆渡人”。陈卓/摄
2月22日18时10分,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妇魏利静顺利生产,助产士把孩子递到她面前。魏利静由一支名为“W大武汉紧急救援队”的志愿者车队送至医院,该车队5名成员专门接送缺乏交通工具的待产孕妇,成为“新生命的摆渡人”。陈卓/摄
赵迪:印象比较深的是《隔离点的故事》这组。新冠肺炎治愈者出院后需要在隔离点进行14天的隔离观察,如果最后核酸检测是阴性就可以回家了,也有一部分人会有复阳的情况,他们将会被再次转送到医院进行治疗。所以人们在这里的心态是期待而又复杂的。采访期间我遇到的一位在观察期核酸复阳的女士,她30岁出头,父母和丈夫都不幸得上新冠肺炎,她的最后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显示阳性。采访中可以感受到她的整个心态都崩塌了。
 3月14日,湖北大学康复驿站,在等待拿饭的间隙,康复隔离人员们短暂交流。赵迪/摄
3月14日,湖北大学康复驿站,在等待拿饭的间隙,康复隔离人员们短暂交流。赵迪/摄
 2月27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医务人员张清抬头查看楼上的情况。赵迪/摄
2月27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医务人员张清抬头查看楼上的情况。赵迪/摄
史阳琨:”跳东湖“这张照片拍摄于4月8日武汉”解封“的第一天,当天下午4点多我开车到武汉大学凌波门附近,看到有两个人赤身在岸上,我就把车停在路边跑过去拍照,回来还被贴了个违章停车的罚单。
 4月8日,武汉“解封”首日,两名男子纵身跳入东湖。史阳琨/摄
4月8日,武汉“解封”首日,两名男子纵身跳入东湖。史阳琨/摄
3.在国内外的疫情报道中,你印象最深的照片/影像是什么?
鲁冲:我印象最深的是史阳琨拍的《跳东湖》。不知道为什么,这张图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两位穿着白色泳衣的少女,后来才发现并不是。
“跳长江”和“跳东湖”对武汉人来说就像是不成文的民间习俗。我在疫情期间也去跳了东湖,和图中跳水者同步且专业的身姿不同,我跳得很滑稽。这张图片拍摄于4月8日武汉“解封”首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跳台”上摆放了一捧鲜花,然后两人同时入水。我不知道图片背后的故事,但这张图给了我很多想象,意味深长。
史阳琨:农历大年三十晚上,网上流传的一个女医生/护士崩溃痛喊“我受不了了”的手机视频。它比当时新闻的照片都显得真实。
钟锐钧:我能说是疫情全球蔓延初期一组美国的片子吗?《New York
Tough》。它跟我们在国内拍的扫街的片子太不一样了,每个摄影师有不同的观察和表达方式。有一张特写我很喜欢,拍的是纽约地铁里乘客隔着纸巾握扶手的照片,有种超现实的感觉。国内摄影记者拍的东西经常会让人觉得有些趋同,这可能跟国内疫情防控比较严格也有关吧。

美国摄影师Hannah La
Follette Ryan拍摄的疫情期间纽约地铁上乘客的手。
李峥苨:印象最深的是《财新》周刊摄影记者蔡颖莉在武汉”封城“前进入武汉红十字会医院拍的一组照片。记者冒了极大风险,在很短的时间内记录下了这次疫情过程中最特殊的一个阶段。现在看来,这些照片记录的正是大家正在迅速淡忘的一些事情,更显珍贵。
赖鑫琳:印象最深的是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拍摄的一张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的鸟瞰图。当时新华社制作了一张海报叫“生命之舟”,海报的设计和形式感加强了我对这张照片的印象。

2月17日,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4.你以前有参加公共突发事件报道的经历吗?这次疫情摄影报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最终是怎样解决的?
赖鑫琳:我做记者13年,一直在跑一线,参与过很多重大公共突发事件的报道,有地震、水灾、龙卷风灾害等等。
这次疫情报道困难重重,刚开始到武汉无法进入病区采访,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才有了突破。在病区里穿着防护服佩戴护目镜采访也很难,护目镜起雾完全看不见,佩戴N95口罩时间长了也会造成缺氧反应,好多次都是忍着头痛欲裂坚持采访拍摄,差点就呕吐在口罩中。

2月16日,武汉,为了近距离记录8名上海120司机组成的急救车队的故事,赖鑫琳跟随车队一天穿梭在武汉各处转运新冠患者,期间穿了8个小时的纸尿裤、5个小时的防护服,在护目镜起雾、完全看不清楚的状况下完成采访拍摄。

赖鑫琳在病房拍摄。
除了生理上的难受,也要背负很重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各种ICU病房,直面病毒还是有很大风险的。
鲁冲:我之前没有参加突发事件报道的经历。这次遇到了不少困难,从早期的出行问题,到后面采访遇到的困难,甚至说心理上的困难都很多。很多其实都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只能不断尝试、摸索,打听其他同行前辈在遇到类似问题的时候如何处理。

2月24日,武汉市武昌区的一家酒店,志愿者张宇枫在为运输物资的司机姚辉理发。鲁冲/摄
赵迪:我之前有报道过地震、爆炸、洪水等突发事件的经历。在其他突发事件的报道中,很多情况都是可预见的,这次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病毒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自己之前也没有关于这方面防护的知识或培训。
说困难的话,我去的时候武汉市内交通已经停运,我不会开车,所以很多采访都是依靠自行车,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要么就是靠同事开车带我过去,总之在做采访之前首先要考虑交通(是否能到达)的问题,然后才会考虑报道本身的内容。北京的公共交通实在是太发达了,开车可能不是必须的,但经历了武汉的疫情报道,我开始考虑学车这件事。

医院中身穿防护服的赵迪(左)。
钟锐钧:2008年我就去报道过汶川地震,当时很多房子都不能住人,大家都在街上住帐篷,或是在临时安置点,所以想在街上找个人采访是很容易的。
这次武汉的情况恰好相反,街上一个人没有,所有人都在家里,想采访只能想办法联系进社区,这还是挺有挑战的。所以早期我选择跟着广东医疗队,这样至少汉口医院的题材是不会缺的。
李峥苨:没有相关经历。困难之一是在采访中发现,好像大家都渐渐有了一些“媒体素养”。关于疫情的很多新闻图片和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人们“比V”、拥抱、鞠躬、作揖、竖大拇指、唱歌跳舞等场景,可能也是一种真情流露吧。但很多人看到镜头会下意识地“比V”,我视力不是特别好,有时拍完照片,回去看大图,才发现角落里有只剪刀手。
人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是这些,可能就认为媒体寻找的就是这些。也见到过几次同行指挥患者对着镜头挥手等。还有采访对象会主动指导,或者主动提醒“你拍这个能发吗”。这些情况让我觉得拍摄更难,也意识到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新闻摄影已经不等于真实了。

3月24日,武汉市江汉区汉来广场附近的小区内,一名外地租户在帮邻居理发。这附近是武汉规模较大的一家建材市场,聚集了许多外地商户、租户。李峥苨/摄

1月31日,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数十名医务工作者在仓库门外等候领取物资,临时被征用作仓库的展厅中堆放着当日到达的各类物资。李峥苨/摄
沈伯韩:我曾参加过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报道。这次疫情报道中,最大的困难是我在当地人生地不熟,有些线索无法顺利获得,拍摄内容的广度会受到影响。因为新冠病毒是一个无法直观看到的存在,再加上外地人的身份,因此在与当地人打交道时,总觉得会有一层口罩之外的“隔膜”、警觉存在,拍摄内容的深度也会受到影响。
5.此次疫情中,你是否带着某种使命感去拍摄?你认为摄影报道在疫情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赵迪:说“使命感”有点太高了,但对于这次疫情报道来说,在整体背景下,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是过去就不再有,它们都值得去记录。对于摄影报道来说,摄影只是一种表达形式,它或许可以帮助更加有真实感的呈现现场。
鲁冲:谈不上使命感,照片可以背负为现实作证、为历史留存的使命,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真按下快门。我认为摄影报道的作用是能为大家提供相对真实的信息,而且有力量的作品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给人反思和警醒。
钟锐钧:说不上,我只是觉得作为一个记录者应该尽可能接近现场。
史阳琨:我没有任何使命感,也没想要拍到什么好照片,我就是想去体验和经历一下。摄影报道呈现了事件的一个侧面,它看起来更真实,但也更容易被宣传利用。

4月9日,武汉市中心医院一楼大厅。史阳琨/摄
赖鑫琳:在封城状态下,这些照片更多的是为将来而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种使命感。我想我们的照片还是传递了很多信息,也传递了很多温度。
李隽辉:没有使命感,我只是个摄影记者,报道是我的工作。
陈卓: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只采访了这么一点人,他们就像这个事件中的碎片,我捡起了这些碎片,加上别人的,一起还原记录一下这段历史,仅此而已。作用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
遇到这种大的事情,肯定有一种职业兴奋感,但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说,我又觉得我们这个职业不太道德。你虽然把很多正能量报道出去给大家信心,或是把悲惨报道出去引得同情,但对这些个体来说,还是很不公平的。我们靠这个职业换取稿费,其实我宁愿不要这份稿费,不要发生这样的事。当记录下来却无法改变对方处境的时候,也会觉得很无力。有时我会用个人关系帮他们联系一些资源和帮助,但这也超出了我作为记者的职责范围了,就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吧。
沈伯韩:说“使命感”有些夸张。我是一个摄影记者,遇到这样重大的事件,如果不能去第一现场,我会遗憾和后悔,那种感觉很不好。所以,我坚持申请去武汉工作。如果未来某一天,人们回望这段时光,我的照片和文字能帮助他们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疫情、武汉和武汉人,那我的工作就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