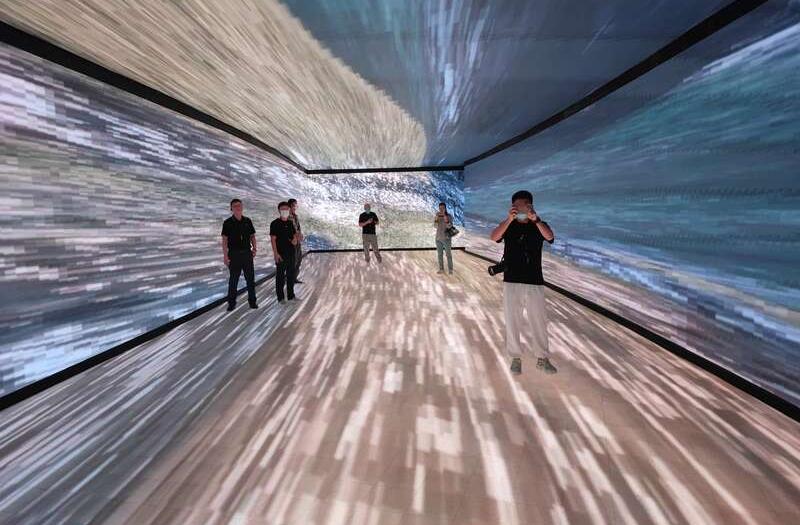科技成果转化利好,创新者站在时代C位

2021年5月14日,辽宁沈阳,在辽宁燕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在调试纤丝敷膜仪。据了解,该公司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打造产学研基地,对众多知识成果进行研发转化,生产获国内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医疗设备。视觉中国供图(资料图片)

2021年11月15日,在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一家生产环保产品的文创企业,工作人员正在检查3D打印产品的干燥情况。近年来,河北省廊坊市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积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激发经济发展新动能。视觉中国供图
4年前的夏天,科技部三定方案出炉,一个新的内设司局——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成立了。这个并未引起太多人注意的变动,为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的再次利好埋下了伏笔。
一段时间以来,我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饱受诟病,不少投入较大的科研“成果”,沉睡在实验室里沦为“陈果”,有的科技工作者还在探索科技成果转化的道路上,碰到了诸如激励不到位、国有资产流失风险等体制机制性障碍。
随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的推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实施,以及科字头机构改革等配套措施落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情况迎来巨变。
7亿元——这是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发的半导体激光技术以作价投资的形式,向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合同金额。
5.116亿元——这是由四川大学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等21项科技成果以作价投资的形式,向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合同金额。
5亿元——这是湘潭大学研发的新型固体酸催化材料技术以许可的方式,向企业进行成果转化的合同金额。
“随着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各高校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已进入平稳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持续活跃,多种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均呈上升趋势。”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科技评估中心副主任黄灿宏说。
前不久,他所在的单位发布了《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其中提到2020年,我国3500多家高校院所的合同项数超过46万项,合同总金额1200多亿元;高校院所创设和参股新公司数量为2808家,比上年增长28.9%。
这些数字的背后,不少科研人员正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实现“名利双收”。随着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分配制度的明确,一批创新者站在了时代C位。
专利“虚胖”
过去这些年,我国科技创新取得长足进步。以专利为例,2021年授权发明专利69.6万件,实用新型专利312.0万件,PCT国际专利申请7.3万件,专利数量连续10年全球第一。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专利数量存在‘虚胖’。”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检测技术创新团队首席王静说。
她曾做过一个有关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难的调研,其中发现,前些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4.7%,其中,企业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44.9%,科研院所为11.3%,高校为3.8%。
“这一结果与智力资源集中、科研经费充足、科技成果丰硕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形成巨大反差,急需深入研判高校和科研院所成果转化效率低下的深层次原因。”王静说。
作为我国首个专注于硬科技创业投资与孵化的专业平台,中科创星在过去近10年,接触过上百家高校院所,结识了不少科研人员。
中科创星合伙人郭鑫发现,有的科技工作者并不愿意迈出创业这一步,甚至不愿意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拿出来进行转化。
在他看来,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主观上没有动力,一个是客观上没有支撑。前者来自评价,高校既要教书育人,又要做科学研究,科研机构主要职责也是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以及“发表论文”;后者来自体制机制“关卡”,创新和转化各个环节衔接不够紧密,还存在不少“孤岛现象”。
王静通过调研和实践,也发现了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困难和障碍。其中一个就是成果培育和转化机制不完善,缺乏技术工程化途径。
“虽常有某一科研领域‘点’的突破,但缺乏技术工程化、系统化和供应链整合的平台和能力,难以跨越技术到商品的死亡鸿沟,导致大部分‘高新成果’束之高阁。”王静说。
她也认为,成果转化队伍与机构建设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在成果转化过程中,既懂科技创新规律,又懂市场商务实践,且懂法规制度的“专业人”“明白人”稀缺。
“要实现成果转化,往往要把科研人员‘逼成’专业转化人员,试错成本奇高,甚至有牢狱之灾。这些问题使很多科研人员对成果转化只能一再观望、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王静说。
转化“三部曲”
被称作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三部曲”的制度性安排,就此拉开序幕。
第一部是法律修订。2015年9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通过审订。后来,有人称之为中国版拜杜法案。
1980年,拜杜法案由美国国会通过,1984年又进行了修改。有人说,这是“美国国会过去半个世纪通过的最具鼓舞力的法案”。法案出台后,一条快速通道在美国科技成果和市场之间架起,并有了后来的硅谷和著名的波士顿128公路的蓬勃发展。
于是,当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出炉后,有不少专家希望可以借此看到中国硅谷的崛起。
201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又出台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
至此,“三部曲”一一落地,但有关的政策利好并未止步。
2020年10月,科技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40家单位全面启动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工作,并以改革试点为契机探索机制创新。
这其中,上海交通大学构建了以成果转化为核心的赋权三段式决策链,明确成果转化流程,实施教师创业企业阳光化行动,解除教师创业的后顾之忧;复旦大学按照重大科技成果和非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分类赋权,并加强了对科技成果转化赋权后的管理和服务;南京大学向在校外建设新型研发机构的科研人员团队赋予职务科技成果的长期使用权,降低向该新型研发机构许可知识产权的门槛……
2021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对外公布。其中要求,要加大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力度,强调科技成果转化收益要对职务科技成果完成人和为科技成果转化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给予奖励和报酬。
“这些政策出台后,科学家的热情被极大激发。”郭鑫说。
在成果转化道路上,人是最关键的创新要素。在他看来,科技成果的产生、转化,发挥至关作用的还是科研团队,如何激励他们,“三部曲”作了相关规定。
过去高校院所的主要任务是“产出成果”。根据原有规定,这些成果产出后归单位所有,在使用、处置以及分配收益时,主要还是由单位负责。新规出来后,科研团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科技成果转化净收益的50%或者股权的50%,都可以归团队所有。
根据《中国科技成果转化2021年度报告(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篇)》,在2020年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合同中,奖励个人金额占现金和股权收入总额的比重超过50%,奖励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金额占奖励个人金额的比重超过90%。其中,个人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为55.9亿元,比上年增长4.8%;研发与转化主要贡献人员所获现金和股权奖励达52.6亿元,比上年增长8.9%,显示出近年来国家相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对于创新人才的激励作用。
科技部成果转化与区域创新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数字体现了科研人员的付出、努力和热情,也体现了科技创新成为真正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产业“拐点”
多年前,中科院沈阳分院做出一个“大胆”的举动——将该分院系统单位100个专家团队的信息毫无保留地公布在网上,包括团队信息、团队介绍和典型项目案例,甚至科学家或课题组联络人员的手机号码、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也都“晒”了出来。
这在中科院系统内部是第一个,其目的就是试着“破除”致使科技成果束之高阁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突围”之难可见一斑。
王静曾建议,设立各级或第三方技术评估和转移转化机构或平台,让科研单位“敢于转”。她告诉记者,科研人员大都是“专才”,不是“全才”,需组建由技术、法律、金融、管理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机构或平台,负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和管理,提供精准全方位的服务,降低行政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的法律和商业风险,扭转专利所有权人怕承担风险而“不敢转”的局面,走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如今,这样的建议正在一些高校院所落地。
在上海交通大学,有一支科技成果转化专员队伍,他们为师生员工提供全流程、规范化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北京大学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共建新型校企联合实验室,与地方政府合作建设异地科研机构,帮助大学原始创新跨越“死亡谷”;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实施大型骨干企业引领战略,与众多大型骨干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促进高效率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2013年,中科创星团队发起成立国内第一支专门针对硬科技的天使投资基金,投资领域覆盖光电芯片及半导体、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医疗、先进制造、新能源等,已形成光电芯片、新能源等产业集群。
在郭鑫看来,在当下硬科技发展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强肌壮骨,把更多金融血液输送到各个关键环节,避免脱实向虚,以支持骨骼与肌肉的健康成长,进而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今,中科创星已投资了超过370家硬科技企业。
2016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的实施举行新闻发布会,时任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谈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还有另一种理解:科技成果转化,转化的往往就是一些颠覆性技术,特别是有可能带来产业“拐点”的技术。
他举例说,柯达胶卷变成数码相机,CRT显像管变成电视机……在他看来,这些新技术所转化的,不仅是价值的问题,还直接关系到国家在产业竞争方面抢占先机的问题。
“我们要让创新创业、成果转化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成为科研人员实现自己价值的一个选择。”王志刚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邱晨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