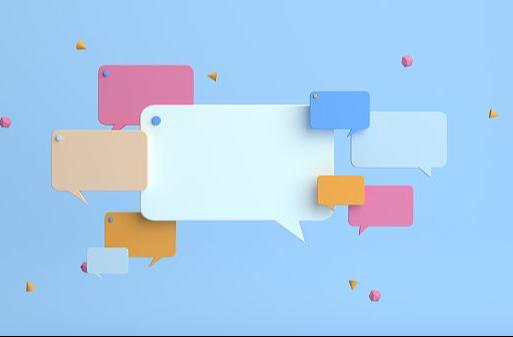飞旋的温烙歌
大学里减肥,得到的比减掉的更多
李雅娟
记得大学开学军训时,体重令我格外尴尬。自己从小就胖,原本只是微胖,但大人闲聊时聊到无话可说的地步,总是把话题拐到我身上,于是“胖”这个形容词像烙印一样打在我身上,也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在日常生活里,体重似乎只存在于买衣服等少数时刻,其余时候可以自欺欺人地假装问题不存在。
但在军训时,它的存在感拉长到十几天。瘦削的同学们穿着迷彩服,英姿飒爽。我呢,又黑又胖,怎么看都像伪军,在全新的生活里,这个陈旧的痕迹格外令人丧气。
同学们刚混熟,室友阿琪打算参加几个月后的马拉松,晚上拉我一起去操场跑步。
阿琪比宿舍里其他同学大一两岁,有主见、长得漂亮、待人和气,整个宿舍都把她当大姐。大姐叫我一起去跑步,我当然乐意跟着去。
至今记得那个冬天。夜晚的大学操场上,漆黑一片,有练武术的、踢球的、跑步的。
我跑得气喘吁吁,感觉肺都要炸了,一看时间,居然才过了四五分钟。阿琪说再跑一会儿,我咬牙接着跑。热了,脱下羽绒服,穿着毛衣继续跑。
当时感觉这15分钟格外漫长。
回宿舍的路上,抱着羽绒服,踩着地上干枯的梧桐叶,腿都有点发软。看着路上悠然漫步的同学,忽然生出一种豪气,仿佛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从那以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可以主动去锻炼。
阿琪后来有没有参加马拉松,我已经记不清,但我的生活确实因这次偶然的运动而缓慢改变。
过去,除了中学里迫不得已的课间跑操,我从没主动跑过步。读小学时,大姨好心让我多跑跑步、减减肥,我却在心里埋怨她当众揭我的伤疤——看,固定思维多么害人,明知道自己缺点在哪儿,却又固执地认为这无法改变。
读高中时,每天学习十几个小时,常常觉得饿,一加餐,又胖了不少。
有次路过药店,趁左右无人注意,赶紧跳到门口的体重秤称了一下——150斤。
走入大学,生活突然没了明确的目标。似乎条条大路通罗马,又似乎条条大路都走不通。
高中时,每天钉在凳子上,一边写那些怎么都写不完的试卷,一边听老师的承诺:“等上大学就好了”“上了大学想怎么玩儿就怎么玩儿”。
大学开学不久就发现这是个谎言,大学里的化学、数学比高中难太多倍,高中只需要背背简单的化学反应式,数学物理也有套路可循,可是有机化学,同一个分子式有各种不同的结构,有的像椅子,有的像船。更何况,在那个全是医学生的校区里,多玩儿一会儿都是罪恶。
社团也令我望而却步。
乐器类社团,招新时要看经验,自己只会最简单的笛子,不敢去报名;体育类社团,我肢体不协调、长得又胖,总怕被人嘲笑……
这些固化的思维和多余的脂肪一样,牢牢附着在我身上。
那次偶然的跑步,像一团小小的火焰,融化了坚冰。
我开始试着晚上去跑跑步,打开几首英文歌,跑3首歌、5首歌的时间。
大二那年,我作为交换生来到陌生的南方城市。一个又一个晚上,我独自在操场上跑步、跳绳,半小时、40分钟、50分钟、一个小时……一圈又一圈,跟着歌曲的节奏加速、减速。
掉秤最快的那几天,隔两三天就掉半斤。终于有一天,一个整天埋头看美剧的室友惊异地问我: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减掉多少斤了?
那时,我不知不觉减到120斤,第一次发现自己的下巴没那么圆。
在放飞自我的那一年,看了许多跟专业课无关的书,去听感兴趣的讲座,学喜欢的语言,买报纸,了解社会……在一次次对专业课的短暂逃离中,探索自己的兴趣。
如果说减肥这件事有什么更重要的价值,大概就在这儿了: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掌控力,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能改变持续十几年的状态。
在令人困惑的大学生活里,减肥让我得到一个支点,体会到掌控感。
临近大四,我放弃了准备了多半年的出国考试,决定考新闻学的硕士研究生,打算将新闻作为自己的志向。
冒出这个想法后,我兴奋不已,当时正在读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顿时感觉找到了书中所说的“天职”。
学习曾是大学里最枯燥的事,柳暗花明之后,发现学习新知可以如此快乐。
之后就是“差生逆袭”的老套剧情,电影中往往用快镜头一笔带过:早上六七点钟起床,学到晚上10点钟自习室关门,备考的短短半年,读了50多本书,成功上岸。
在新学校,我延续了跑步的习惯,绕着学校所在的小岛跑一圈,大约20公里。在内心充满不确定的时候,专注地跑步让人安心。
至于体重,这些年起起落落。自从瘦下来之后,就对“胖”这个字脱敏了,也不再像阿Q讳言“秃头”一样讳言所有跟它相关的词语。
这些变化,也一点一点地改变了我过去固化的思维。多数情况下,人总有改变的余地,只是这个过程中的艰辛和孤独,常常让人难以忍受。多一点努力和尝试,总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