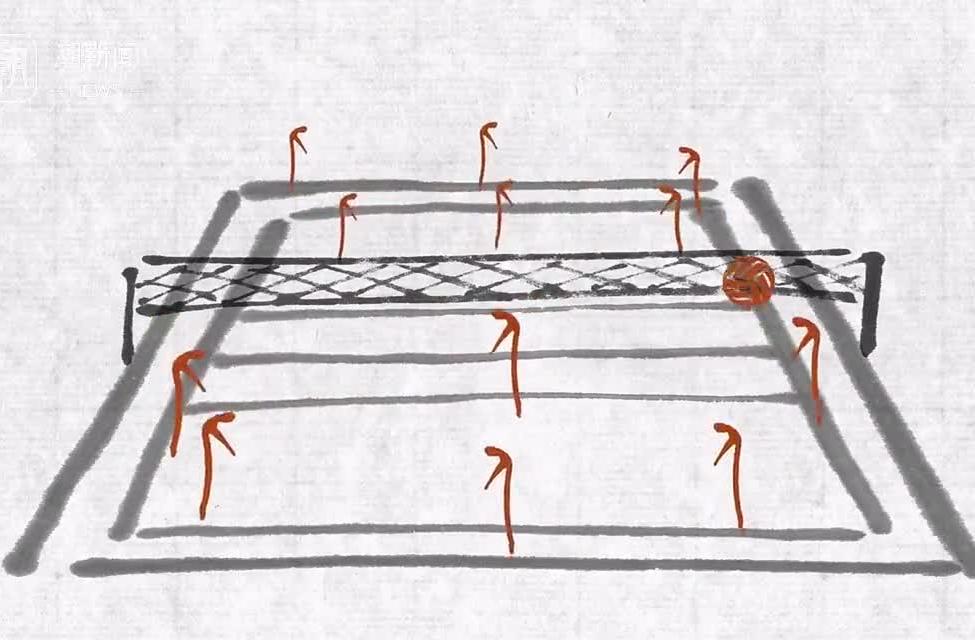妈妈上班去
产假结束的第一天,我就立刻坐回到电脑前,渴望过去几个月为哺乳摄入的过剩营养迅速转化成工作的洪荒之力。
我做足了全面复产复工的准备,调整孩子的作息与我工作的时间匹配,准备好奶瓶和温奶器,这样即便我一时抽不开身,他也可以吃到存在冰箱里的口粮。为了提高效率,我甚至主动给编辑提出了交稿“死线”。
但事实上,我低估了生育带来的影响。我很难长时间专注地托着脑袋写作,每3个半小时要吸一次奶;孩子会突然哭闹,我的时间和语言都被切得稀碎;睡眠不足,身体像一辆破车,预热很久才能发动,刚驶上快车道,孩子又哭了。
一个人的时间和耐心总是有限的。我能怪孩子吗?不能,他的笑是治愈我的良方。
“我要被淘汰了”,我在电话里大声对我妈讲,“我可能马上就会收到职场‘给妈妈的罚单’!”
我出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那时“停薪留职”一词正兴起。我妈和王健林、潘石屹等人一样,都提交了“停薪留职”申请书,只不过人家是去创业,我妈回家看娃。她有几年全职在家,重返职场时,和她同批工作的同事都成了她的领导。我妈不想我走她的老路。
我花重金请了带孩子的保姆,家政市场上,她们是炙手可热的“育儿嫂”。我工作上稍松一口气,工资就付不起育儿费用。
网友替我算过一笔账,在北京,没有老人帮忙照料孩子的双职工家庭,每个月支付给育儿嫂的费用约9000元,高于北京市2022年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水平8711.83元。按照孩子3岁入幼儿园计算,三年的育儿嫂支出超过30万元。这仅仅是养育孩子的九牛一毛。
在带娃这件事上,国内外女性面临的困境差不多。我查到的一份国外研究显示,在美国,生完小孩后,74%的职业女性会不顾一切重返职场,40%的女性会继续从事全职工作。离开职场一年,女性的年平均收入将下降20%,女性“驶离职场高速路”的平均时间是两到三年。产假时间越长,上班族妈妈和爸爸之间的收入差距越大。
我感慨,养一个孩子的难度是普通本科,两个就是“双一流”高校,三个无异于考上清华北大。七个,就是欧盟主席了——我还在月子里,我丈夫给我发了一条信息,“和马克龙一起访华的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女的,养育了7个孩子。”
“7个孩子”被写进新闻标题。这似乎是女性的“特权”,也是一个传统的性别角色陷阱。就像成功女士接受采访时,都要被问“如何兼顾工作与家庭?”
接手养娃这项需负责、辛苦且重要的系统工程后,我们不得不将手里的事项重新排列组合。为了适应生活里多出来一个一刻不停的小生命这件事,我丈夫冒着丢失大客户的风险,努力把每周的应酬和出差精简到个位数,平均每天可以挤出来半个小时亲子时间。
产后激素的剧烈波动和养娃的疲惫让我时常成为家庭战争的发起者,我在又一次独自深夜哄娃后崩溃大哭。大数据比我丈夫还能共情我的情绪,经常在App首页为我推送“为什么产后第一年是离婚高发期”。
我刚出月子就在研究托育机构。有同事建议我搬到郊区去,她们考察过,那有家不错的托育园,只不过大人通勤单程要3个小时。另一个朋友在今年秋天换了工作和生活的城市,新单位为员工配套了托育机构。
一群去托育园考察结束后的妈妈们心动不已,但大多没能越过重重阻碍。有的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不具备决策权;有的担心送孩子到托育园,被人说“不是一个好妈妈”——社会对母亲有传统期待,母亲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是偷懒、不负责任的表现。
社会科学发展两百年了,为什么这些期待还“裹着小脚”呢?诸多研究结果显示,母亲专职照料的孩子和那些由母亲和其他人同时照料的孩子在个体发展上并无不同,连母子感情方面都没有什么差距。而父母的行为因素,以及父母婚姻感情亲密度这些因素对孩子的影响比任何形式的看护照料要多出2-3倍。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
2021年,浙江省教育厅印发全国首个关于教育幼托班管理的指南,随后又在17个县设立普惠托育首批试点。备孕的同事跃跃欲试,对幼托事业的发展极有信心。
我强打精神,尽管又在电脑前枯坐一天,但觉得起步慢一点没关系,在职场的高速路上,踩稳油门,要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