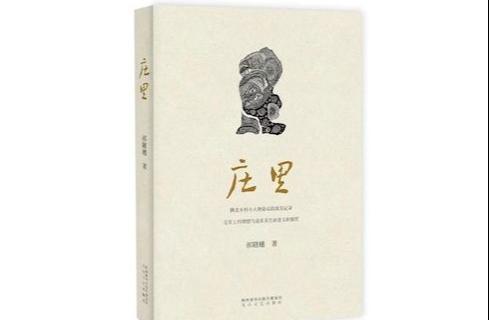刁亦男遇见双雪涛:存在主义的落脚,浪漫主义的余韵
2014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获得当年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虽然此前已经拍过两部电影《制服》和《夜车》,但到此时国人才第一次有机会在大银幕上了解这位导演。黑色电影的类型嫁接风格浓烈的作者化表达,破亿的票房成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的“文艺片天花板”。刁亦男就如同横空出世一般填补了中国电影的部分空白。
也是在这一年,作家双雪涛开始写作小说《平原上的摩西》。这位前银行职员将他在东北成长三十多年的经验一股脑倒进了这个发轫于艳粉街的犯罪故事里。而从那一年开始,双雪涛几乎每一年都会看一遍《白日焰火》。
他们的作品先于本人惺惺相惜,很多年后,也终于达成了电影上的合作。
4月17日,作为第十三屇上海双年展的特别呈现单元,由实验影像中心(CEF)、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联合主办的特别放映活动上,导演刁亦男和作家双雪涛展开了一场主题为“暗处里寻找微火”的主题对话,从各自的经验谈及对于创作和人性的体察。
 刁亦男(左)与双雪涛在对谈现场
刁亦男(左)与双雪涛在对谈现场
《白日焰火》的成功是随波逐流被裹挟的结果
对谈开始前,是一场《白日焰火》的放映。这部拿下柏林金熊的电影是距离当下最近的一部欧洲三大最高奖项的影片。
一场罪行之后,白昼的天空中升腾起炽烈的火焰,在艺术展馆里观看的氛围与电影院似有不同,影像本身所承载的寓意和纯粹感受较之文本和叙事,有了更直观的冲击力。
 《白日焰火》海报
《白日焰火》海报
《白日焰火》的出现标志着刁亦男电影创作的成熟,展现出他独树一帜的作者性。在一个上升的时代氛围中,他却敏锐地把握住世态人心的无所依傍,将其外化成自己笔下那些向死而生的边缘人。死亡在他的电影不代表终结,而是一种对绝望的彻底反抗。
谈起这部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于中国电影都十分重要的作品,在此之后,刁亦男被视为一个能够融合艺术化表达又兼顾商业诉求的导演,之后一部更为“存在主义”叙事的电影《南方车站的聚会》由于胡歌的加盟而一早就备受关注。刁亦男却调侃,《白日焰火》的成功是一场“被裹挟”的结果。
 《南方车站的聚会》海报
《南方车站的聚会》海报
观影的过程让他想到十年前的这个时候,项目刚刚提上日程。他早就想拍侦探片,但印象里侦探片和自己脑海里的侦探片并不相同,“我脑海里侦探片是作者化而非奇情、惊悚这些元素堆积,所以难找到投资。”反观整个《白日焰火》打磨出炉的过程,刁亦男说,“创作是被市场推动和改变,一步步不断变得通俗、奇情和戏剧化。它并不是一个有概念的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随波逐流被裹挟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开始是很不情愿的,没有一个影视公司的事愿意专门扶植艺术电影导演的,或者也没办法像今天这样因为技术的发展而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完成一部电影,艺术电影也能够有固定且高质量的受众。2011年的环境是完全关注票房的,这就逼得你不得不去迎合,过程中有把原本的设计彻底推翻和自我洗脑的时候。当时我也还不知道电影史上有那么多的那么好的黑色导演。那时候觉得自己是堕落了。”
虽然有某些“被迫”的成分,但如今刁亦男也认可这种被“打磨”的经验是有益的,“所有牵绊和阻碍你的事物最后都哺育了你。”
犯罪本身就是日常关照
邀请双雪涛来与刁亦男对谈,一方面是因为两人最近共同合作的电影《平原上的摩西》,另一方面,两人在此之前的作品中似乎就有着某种微妙互文。
 《平原上的摩西》片场照
《平原上的摩西》片场照
同样都善于描写犯罪,并透过罪案对人物的存在状态作出深刻探讨的两位作者在交流中袒露了对于这个类型外壳极为相近的看法。
“人类本身的存在就与罪有很深的关系,有的罪没有发生,有的发生了。犯罪本身就是日常关照,并不是什么特殊的写作角度。”刁亦男认为描写罪案其实是指向真实,“罪是人本性的展露,是社会的贫富的揭示,同时犯罪承载的戏剧性,是和电影的特性相亲近的。”因此作为一个电影导演,这样的选择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罪行一方面有它合理的和生活的关系,又亲近电影本性,非常适合开放地进入到通俗的语境里,让更多人看到这种表达。”
双雪涛则谈到,“犯罪这个词包含的东西很多,重要的不是类型,是类型上附着的东西是什么,黑色电影中罪案的背后并不是通俗意义上犯罪小说所描写的哪些那些动作,更像加缪、萨特笔下的人物,犯罪外衣下表达的东西,其实是严肃的奇观。作为一个严肃的类型,它可以把人存在的本质探讨得很深。它是一个很强劲的引擎,能驱动前进,在速度和深度上都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两人共同谈到自身创作受到的一些影响,例如存在主义。刁亦男电影中的人物大多带着一种强烈的存在主义印记,关于这一点,双雪涛十分推崇。“《南方车站的聚会》里的存在主义的意味比《白日焰火》更重,在胡歌扮演的主人公的状态里能感受到他哲学上的落脚点。刁亦男的几个电影都有自我选择的过程,这种有很强文学和哲学底座的电影,观看的乐趣是比单纯用视听去驾驭你的那种电影乐趣更大的。”
对于这样的评价,刁亦男也认同,“让电影中的人物投入这样的状态中去寻找自己生命的价值,就是存在主意的诗,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两个人去试探对方的存在和身份,完成一段生命的路程。让人物接近危险,是存在主义所倡导的,把自己交给另一种未知生命状态的旅程。《南方车站的聚会》是我自己治愈自己的手段,怎么去迎接,怎么面对生命的崩溃而勇敢的去驾驭它。”刁亦男说。
 《飞行家》书影
《飞行家》书影
而同样擅长描写在危险边缘游走人物状态的双雪涛,在他的小说集《飞行家》的封面上写着的那行“为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为我们人性中珍贵的瞬间,留下一些虚构的记录。”成为他笔下世界的准确概述。
“我是在这个环境里长大的,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就是我身边熟悉的普通人。我就是普通家庭、普通学校长大的人,那些记忆引导你,得以进入文学的轨道。同时我觉得我的某些篇章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对人物的想象是作家的权利,我不愿意写特别现实主义的东西,因为当你提笔的时候就不可能完全现实,你已经在脑海处理了自己的素材。”
对于“浪漫主义”的畅想也得到刁亦男的共鸣,“我们都多多少少让作品闪现出浪漫主义的余韵,离别是真正的爱。关怀那些脆弱的人,脆弱的时刻,创作者也和普通人一样极其脆弱,我们愿意用这种脆弱去唤醒某种有力量的东西,这种姿态未必带来结果,但这种姿态对于迎接那些焦灼的状态也非常重要。”刁亦男说。

小说是用来读取的,而电影是用来观看的
刁亦男和双雪涛的惺惺相惜在电影《平原上的摩西》中总算得以交汇。尽管刁亦男形容文学之于他的滋养是“嗑瓜子”,双雪涛回应“那电影就是开心果”,但两人高度相近的美学观念和过往作品的力量感都让人对他们的合作充满期待。
 《平原上的摩西》书影
《平原上的摩西》书影
“《平原上的摩西》是我精神世界的反映。”双雪涛这样评价这部对自己极为重要的作品,同时他谈到,自己在写作这部作品的2014年恰好受到了刁亦男的重要启发。“但是在电影院看完《白日焰火》,同行朋友都觉得很迷惑,但我感到了震撼,以为我在观看中发现了一种语法,那个时候我在写作《平原上的摩西》。这部电影给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它让我发现内心的某种东西,好的创作是会引领你,知道你内心的欲望,我当时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和容器。”
今年,双雪涛的另一篇小说《刺杀小说家》刚刚在春节档被搬上银幕。作家笔下的绮丽幻想被呕心沥血磕特效的电影团队做了可谓极致和用心的呈现,但最终也是褒贬不一。文学和电影之间是否有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也成为现场观众抛给双雪涛的问题。
 《刺杀小说家》海报
《刺杀小说家》海报
“电影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当代艺术,它的综合性和能包容的东西非常多,门槛又没有那么高的艺术形式,它可以容纳很多人,对很广大的观看人群施加某种影响。”双雪涛很清楚电影和文学是不同的。
“《刺杀小说家》的电影,它立足点是‘观看’,而小说是要‘读取’的,电影的直接性更强,而且它作为商业电影需要逻辑,小说仅仅通过文字的旋律就能把人催眠,但电影如何把梦境植入观众的脑子,需要更强的证据链,这是不同的构建过程。我觉得《小说家》电影我自己是很满意的。一个好小说搬上屏幕方式有很多,导演处理改编也没有一定之规。”
刁亦男对双雪涛的小说的评价是,“除了有通俗情节的铺排,他还充满尖利于柔软并存的东西,他找到他的文体,这是他的小说与众不同的地方。我感觉是遇到同道中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