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彦斌:回眸中国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
回眸中国百年法治进程
——读《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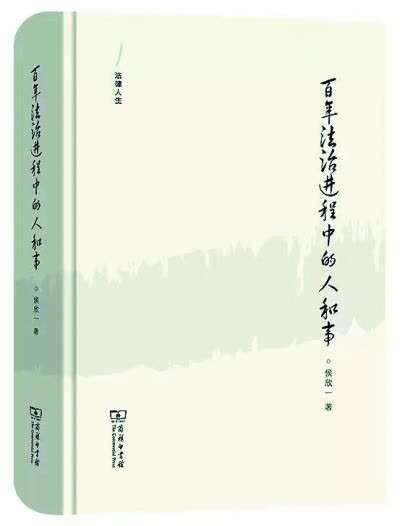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 侯欣一 著 商务印书馆
《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 侯欣一 著 商务印书馆
【读书者说】
时间本是一种设定的刻度,但人类天生的历史感却已将时间视为当然的存在。正因此,从某个时刻算起的十年、百年,人们都珍视并纪念,而对世纪起始的时刻更赋予诸多历史之忧思和未来之寄托。然而,对中国来说,1900年,即20世纪的起始时刻则并非一种空泛的历史浩叹,而是真正与迈向现代社会的大转折密切相连。
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指的是在1900年以前,古老而封闭的中国已经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反应中,逐步被动和主动地与世界发生着联结,这一过程历经数十年之久。表面上看历史事件总是偶然发生的,然而大航海和源自西方的现代工商业注定要从港口进入中国,不会因当时的决策者到底采取封闭还是开放的态度而终止。并且,冲突亦在所难免。重要的是,冲突之后,双方将进入何种新的共处模式当中,以及中国将迎来何种变化。正是在这一输入型的冲击中,中国伴随跌宕而踏上了迈上现代社会之路。
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中国迈向近现代社会始于1840年。其实,现代社会从来都是双向的,它以经济为始,以法律为志;以经济为壤,以法律为苗。中国的近现代进程证实了这一点,先是新的产品和产生方式从港口到腹地,从机械到日用品,当经济之变历数十年时,政治法律之变乃成有识者的集体有意识。正是基于这种识见,侯欣一先生将自己的新著《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关注的起点锁定在1900年前后。
国人历史意识虽强,但说及法律的历史则不免茫然。何止坊间不寻法史之味,即使法学界也并不常以法律史为聚焦。问其因,就一般读者而言或与人类之娱乐天性有关。娱乐之心,促使一般读史者往往关注宫廷故事、战争风云与儿女情长;对于严肃的读者,一则由于历史上法治大多不彰,二则好的法律史作品相对缺失,于是其注意力大都被政治史、军事史,乃至经济史所吸引。笔者以为,娱乐自亦好事,足以放松心情和感受美好,但今日影视与互联网之娱乐供给早已充足,人们亦不妨将影视与互联网和书籍略做分工,以影视和互联网怡悦心灵,以阅读图书哲史凝练,做理性之思。以理性之思读史,特别是法律史,不妨从《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一书开始。《百年法治进程中的人和事》(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版)的作者侯欣一先生是法律史名家,全书是一部专题式的学术随笔集,以中国传统的白描手法,将一个个鲜活的法治人物和精彩纷呈的法律事件从沉默的历史中打捞出来,呈现在读者面前,揭示法治与百年中国复杂而真实的关系,为读者思考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一个新的坐标和视角。
中国近现代法治的历史进程极为复杂。一百年前,中国现代社会确实有了大的转折,即清末修律之赫然启动,现代法律制度由此出现。然而,表面上看,百年来的历史却依然上演着一个个法史之外的故事。例如在辛亥革命当中,虽有《临时约法》问世,虽有挚爱宪法的宋教仁等人对其钟情之事业的投入,然而,若按以往人们的观察,都比不过野心、雄心和个人私欲在历史现场的挥发。人们更关注枪炮作响,并不甚操心法律之有无声息。百年当中,当枪炮在一段时间作响时,社会进入战时状态,救亡更加压倒法治之梦。
若将此法史以外的故事放在法史以内,则可知,当社会之运行逸出法律以外时,则不免以失序带来新的失序。以往人们曾关注过“依法而治”和“以法而治”,也就是“rule of law”和“rule by law”的差异,学者林毓生将前者译为“法律主治”,前者是权力在法律之下,后者是法律为权力所用。由此,后者就很难称之为法治,而乃为权力之治,法律就化为权力意志的替代品。在以法治为视角的法史看来,尽管历史纷纷扬扬,无非是法治的寻梦之旅和受挫之旅。事实上,即使是更长的千年万年法史叙事,若不以此为视角,则其所呈现的,也无非是不知何以然的古旧法条。核心来说,法治所关注者,是权力与权利,自由与秩序之均衡,这种均衡本来不能轻易达到,何况非常时期时势紧张。当枪炮与运动兴起时,一方面是权力将用以调集资源,秩序将用以划一步骤,另一方面是权利和自由不仅受限,还失去了经济生活的寄托——经济流动在非常时期大大受限,由此,命令往往代替法律,意志往往代替法意。如此这般,不能不让现代社会中标志性启动的法律进程遭遇极大受挫感。显然,这个百年来的特性,侯欣一先生在此书中已捕捉到。
法史的故事不仅是嵌刻在历史中的故事,即枪炮声中的孤独法治故事;不仅是驯服权力、约束权力的故事,即权力压倒权利的故事;不仅是以真实的雨点般案例彰显法治不昌则社会失序的故事,还是理念的故事。所谓理念的故事,就是人们并不天然地全部赞成法治,而将在歧见层出的纷争话语中各持己见,即使是对于社会当中的每个人,总体也分为面向整体还是面向个体,关注团体还是关注个体,赋权于集体还是赋权于个体,即使不是非此即彼,也呈现较大的理念分歧,这当然也都在百年当中的法律史中,有些隐而不发,需要探其幽微,有些明示于市,值得深挖其道。侯欣一先生笔下的不同法律事件和人物,也都试图予以钩沉。
或许我们可以说,人们的“娱乐”天性,即阅读战争、冲突甚至宫廷故事的天性——无论来自影视还是书面文艺作品,也为我们阅读法律史作品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前提,有助于让我们思考在冲突和战争来临前,什么才是解纷和弭兵之道——这就是法史故事所呈现的法治故事和法治理念。事实上,当百年前清末修律时,现代社会的核心要素——也即新型法律的崛起,已经刻下了这些理念,即使后来遭遇波折和分歧,依然内在地不改其志。我想起一句古诗“心火因君特地燃”,法治便是有识者们的一腔心火,侯欣一先生在此书中试图捕捉百年来的不灭心火。
侯欣一先生曾经给我分享过一段话,这是17世纪的法国人皮埃尔·培尔在《历史词典》中就历史写作发表的一番评论:“一般说来,写历史是一个作家所能涉猎的最具难度的创作,或者说是最难的一种。它要求有超常的判断,有高贵、清晰而简洁的风格,有出色的道德感,要完全笃诚正直,要有许多极好的资料,并有将它们安排得井然有序的技巧;最重要的是,要有抵御宗教狂热本能的力量,而这种本能会怂恿我们排斥我们认为真实的东西。”或许,这就是他的目标。这个目标达到当然不易,但作为理想却值得奔赴。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提出一个理想主义历史学家的概念。于法史写作而言,一个理想主义历史学家有双重心火:历史心火和法治心火。
(作者:董彦斌,系《现代法学》副主编)
《光明日报》(2020年12月05日12版)









